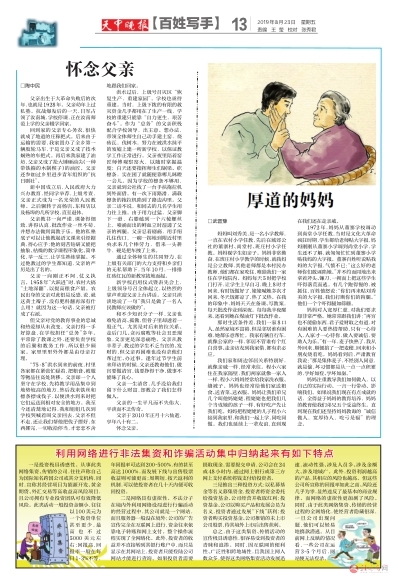发布日期:
怀念父亲
□陶中民
父亲出生于大革命失败后的次年,也就是1928年。父亲幼年上过私塾。抗战爆发后的一天,日军占领了汝南城,学校停课,正在汝南师范上学的父亲辍学回家。
回到家的父亲专心务农,很快就成了地道的庄稼把式。后来由于运输的需要,我家置办了全乡第一辆胶轮马车,于是父亲又成了技术娴熟的车把式。再后来我家建了油坊,父亲又成了抡大锤砸油尖(一种带铁箍的木制楔子)的油匠。父亲还参加过乡里进步青年组织的“抗日剧社”。
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大力兴办教育,经同学举荐,上级考查,父亲正式成为一名光荣的人民教师。之后辗转于高杨店、东和店以及杨埠的几所学校,直至退休。
父亲教书一向严谨,课备得细致,讲得认真,批改作业一丝不苟,并想办法做到寓教于乐。他的私塾底子可以让他教起语文课来引经据典,得心应手;他的刻苦钻研又能把抽象、枯燥的数学课程形象化、简单化,举一反三,让学生熟练掌握。不过他教过的学生都知道,父亲的严厉是出了名的。
父亲一向刚正不阿,仗义执言。1958年“大跃进”时,农村大搞“土地深翻”,以提高粮食产量。农民出身的父亲对此很是反感,说,就这黄土瓣子,没有肥料翻再深有什么用?就因为这一句话,父亲被打成了右派。
但父亲对党的教育事业的忠诚和热爱却从未改变。父亲打得一手好算盘,在学校担任“总务”多年。平常除了教课之外,还要负责学校的后勤和教务工作,所以很少顾家。家里里里外外都是由母亲打理。
“75·8”洪水到来的前夜,村里各家都在紧张忙碌着,把粮食、被服等物品往高处转移。父亲却一个人坚守在学校,先将教学用品集中到地势较高的地方,然后找来铁丝和檩条摽成伐子,以便洪水到来时把它们运送到相对安全的地方。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我和姐姐几次到学校哭喊着叫父亲回去,父亲不但不走,还让我们帮他把伐子摽好,东西挪完,一切收拾停当,才恋恋不舍地跟我们回家。
洪水过后,上级号召灾区“恢复生产,重建家园”。学校也亟待重建。当时,上级下拨的有限的救灾资金几乎都用在了生产一线,学校的重建只能靠“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作为“总务”的父亲积极配合学校领导,出主意、想办法,带领全体师生自己动手建土窑,烧砖瓦,伐树木,努力在被洪水抹平的废墟上建一所新学校,以保证教学工作正常进行。父亲夜里陪着窑匠师傅观察窑火,以随时掌握温度;白天还要指挥师生们锯梁、砍檩条,实在困了就随便靠哪儿眯瞪一会儿。因为学校的檩条不够用,父亲就到公社找了一台手扶拖拉机到外面借。有一次下雨路滑,满载檩条的拖拉机陷到了路边沟里。父亲二话不说,和同去的几名学生用力往上推。由于用力过猛,父亲脚下一滑,右膝磕到一个六棱螺丝上,喷涌而出的鲜血立时湿透了父亲的裤腿。父亲忍着剧痛,用手绢扎住伤口,一瘸一拐地到附近村里央求来几个棒劳力,借来一头耕牛,硬是把车拽了上来。
通过全体师生的共同努力,在上级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和乡亲们的无私帮助下,当年10月,一排排红砖红瓦的新教室拔地而起。
新学校启用仪式暨表先会上,上级领导号召全体起立,以热烈的掌声欢迎父亲上台讲话。父亲只淡淡地说了一句“我只是做了一名人民教师应该做的”。
和不少知识分子一样,父亲也难免清高、孤傲,但骨子里却透着一股正气。尤其是对后来的拉关系、走后门儿、贪污腐败等社会丑恶现象,父亲更是深恶痛绝。父亲从教半辈子,教过的学生不乏当官的、发财的,但父亲再困难也没有求他们帮过忙、办过事。逢年过节学生前来拜访的时候,父亲还教诲他们,做官要做清官,钱要挣得干净,做事不能昧了良心。
父亲一生清贫,几乎没给我们留下什么财富,却教会了我们怎样做人。
父亲的一生平凡而不失伟大,平淡而不乏传奇。
父亲于2010年正月十六仙逝,享年八十有二。
怀念父亲。
父亲出生于大革命失败后的次年,也就是1928年。父亲幼年上过私塾。抗战爆发后的一天,日军占领了汝南城,学校停课,正在汝南师范上学的父亲辍学回家。
回到家的父亲专心务农,很快就成了地道的庄稼把式。后来由于运输的需要,我家置办了全乡第一辆胶轮马车,于是父亲又成了技术娴熟的车把式。再后来我家建了油坊,父亲又成了抡大锤砸油尖(一种带铁箍的木制楔子)的油匠。父亲还参加过乡里进步青年组织的“抗日剧社”。
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大力兴办教育,经同学举荐,上级考查,父亲正式成为一名光荣的人民教师。之后辗转于高杨店、东和店以及杨埠的几所学校,直至退休。
父亲教书一向严谨,课备得细致,讲得认真,批改作业一丝不苟,并想办法做到寓教于乐。他的私塾底子可以让他教起语文课来引经据典,得心应手;他的刻苦钻研又能把抽象、枯燥的数学课程形象化、简单化,举一反三,让学生熟练掌握。不过他教过的学生都知道,父亲的严厉是出了名的。
父亲一向刚正不阿,仗义执言。1958年“大跃进”时,农村大搞“土地深翻”,以提高粮食产量。农民出身的父亲对此很是反感,说,就这黄土瓣子,没有肥料翻再深有什么用?就因为这一句话,父亲被打成了右派。
但父亲对党的教育事业的忠诚和热爱却从未改变。父亲打得一手好算盘,在学校担任“总务”多年。平常除了教课之外,还要负责学校的后勤和教务工作,所以很少顾家。家里里里外外都是由母亲打理。
“75·8”洪水到来的前夜,村里各家都在紧张忙碌着,把粮食、被服等物品往高处转移。父亲却一个人坚守在学校,先将教学用品集中到地势较高的地方,然后找来铁丝和檩条摽成伐子,以便洪水到来时把它们运送到相对安全的地方。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我和姐姐几次到学校哭喊着叫父亲回去,父亲不但不走,还让我们帮他把伐子摽好,东西挪完,一切收拾停当,才恋恋不舍地跟我们回家。
洪水过后,上级号召灾区“恢复生产,重建家园”。学校也亟待重建。当时,上级下拨的有限的救灾资金几乎都用在了生产一线,学校的重建只能靠“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作为“总务”的父亲积极配合学校领导,出主意、想办法,带领全体师生自己动手建土窑,烧砖瓦,伐树木,努力在被洪水抹平的废墟上建一所新学校,以保证教学工作正常进行。父亲夜里陪着窑匠师傅观察窑火,以随时掌握温度;白天还要指挥师生们锯梁、砍檩条,实在困了就随便靠哪儿眯瞪一会儿。因为学校的檩条不够用,父亲就到公社找了一台手扶拖拉机到外面借。有一次下雨路滑,满载檩条的拖拉机陷到了路边沟里。父亲二话不说,和同去的几名学生用力往上推。由于用力过猛,父亲脚下一滑,右膝磕到一个六棱螺丝上,喷涌而出的鲜血立时湿透了父亲的裤腿。父亲忍着剧痛,用手绢扎住伤口,一瘸一拐地到附近村里央求来几个棒劳力,借来一头耕牛,硬是把车拽了上来。
通过全体师生的共同努力,在上级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和乡亲们的无私帮助下,当年10月,一排排红砖红瓦的新教室拔地而起。
新学校启用仪式暨表先会上,上级领导号召全体起立,以热烈的掌声欢迎父亲上台讲话。父亲只淡淡地说了一句“我只是做了一名人民教师应该做的”。
和不少知识分子一样,父亲也难免清高、孤傲,但骨子里却透着一股正气。尤其是对后来的拉关系、走后门儿、贪污腐败等社会丑恶现象,父亲更是深恶痛绝。父亲从教半辈子,教过的学生不乏当官的、发财的,但父亲再困难也没有求他们帮过忙、办过事。逢年过节学生前来拜访的时候,父亲还教诲他们,做官要做清官,钱要挣得干净,做事不能昧了良心。
父亲一生清贫,几乎没给我们留下什么财富,却教会了我们怎样做人。
父亲的一生平凡而不失伟大,平淡而不乏传奇。
父亲于2010年正月十六仙逝,享年八十有二。
怀念父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