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日期:
有根的诗,有愁的思
——郭建光诗歌印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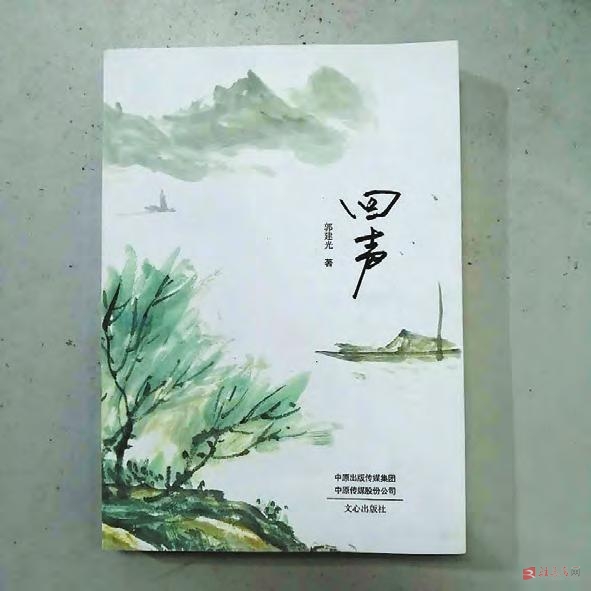
□尹聿
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说过一句很微妙的话:“圣人之情,见乎文辞。”如果把圣人换成诗人,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说:诗人总是在练习如何把对生活世界的感觉(情)转换为诗行(文辞)。诗人与非诗人的区别,在于他能否把生活世界锻造成诗。在对建光诗歌的阅读中,我实实在在感受到他的诗人品质及他锻造世界为诗的能力。他是一个真诗人。读了他的诗歌,印象颇深,谈几点感想。
诗歌是有原产地、有根的
好诗人都是有原产地的。或者说,每一个人,尤其是诗人,都要有故乡,都要有一个精神的发源地,一个埋藏记忆的地方。这个地方,不仅指地理意义上的,也是指精神意义或经验意义上的。但凡好的写作,好的诗歌,它总有一个精神扎根的地方,根一旦扎深,开掘的空间就会很大。建光的诗都是有根的。如果你有耐心细读,如果你有兴趣分辨,就会很容易地找到他情感的根、诗歌的根——就是河南,就是河南驻马店乃至驻马店汝南县,甚而至于驻马店汝南县那个实实在在坐落在大地某一隅的乡村。而真正的根还不仅仅是这些,而更应该包括世世代代生息在那里的人。那方土地养育了他的身,更滋养了他的灵魂,所以才使他魂牵梦绕,
念念不忘。这在他的诗歌中,处处体现,诗集《回声》的《故乡》《远方》《征程》等部分俯拾皆是。比如《木香》《梦里故乡》《汝水》《一座城池一寸金》《铁花飞满天》,直接呈现出故乡的风貌和深刻的儿时记忆以及不绝的忆念。在《从寒露下到霜降》一诗里,传统的二十四节气意象,家乡“一草一木”的意象,构成了“家乡”这个整体的大意象,其营造的诗意尤其迷人。
而在走出狭义的“故乡”后,无论是《人在旅途》中游走齐鲁大地孔林孔庙以及登泰山,还是游楚地黄鹤楼以及广大的秀美江山等,诗人骨子里还是装着故乡,始终是故乡、诗歌和情感最终的落脚点也仍然是他深爱着的故土。并且,在他游走的过程中,急于返乡的情怀渗透到诗歌里:“我要加快脚步加快脚步/回到属于自己的故乡/与脚下的土地/来一个长久的拥抱”(《一颗心在泰山里迷茫》)。
他的脚步朝外,行走远方,而他的心是朝内的,诗歌的情感方向始终是朝向内心的。即使为了生存,写那些出外打工者、漂泊者,虽身在异地,诗人的凝望仍然是心的那个方向。
思乡病与诗歌的现代性
从建光诗歌的家乡情结书写中,我们不难看出诗人对家乡深深的热爱,但在其牧歌般的吟唱和怀念里,仍然埋藏不住自身对远方的渴望。尽管那种怀乡情感是真诚的,记忆里家乡是那么美好,但是从另外一层意思里,我们可以看出,进入工业化时代的今天,外部世界的变化甚至是巨大的变化,也在对诗人的认知产生着巨大的冲击。书写这些变化,拿外部世界和家乡对比也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不得不承认现实存在的残酷性和真实性。家乡有很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这样,便会产生“痛苦”,产生一种“病”。这种病是“乡愁”的一种,也是“思乡病”的一种。其中矛盾的心情是真实的、深刻的,作为真正的诗人,也应该是必须具有的。当然,我在这里说的家乡已经不仅仅指建光的那个具体的乡村以及县市,至少是指向了这个省,乃至中国这片广袤的土地。作为新闻工作者,他是敏感的。在深入了解这个纷繁复杂的社会上,他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有更多的机会接触社会上形形色色的人和事。因此,他的乡愁就赋形在这些普通平凡人物和处于社会底层的小人物身上,最典型的就是“新闻长诗”《一个农民工的传奇》。这是一首大气派、大悲悯的现实主义诗歌。我看重的是诗人写作的悲悯情怀,而这种悲悯情怀的得来,我敢肯定地说,除了诗人“根”的素质品质之外,还绝对来源于诗中人物农民工司令张全收的悲悯情怀。诗人的“愁”是透明的,也是可敬的,他多么渴望有一个传奇的人物来拯救家乡,拯救这个世界,无论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
在建光的诗歌中,类似的诗歌从另外一个角度呈现现实的也有很多,大都是些社会底层为生存挣扎的小人物。比如《应聘的女孩》《坠落的生命》《这个城市的街头》《有一个女孩名叫婉君》等,这些人的遭遇和命运,总让人唏嘘不已。他们的人生细节,总能击中人类情感的软肋,从而让我们对自己热爱着的“家乡”有更深层的思考。这些关注时代和民生的诗歌,是我对建光最敬佩的。
通过以上对建光诗歌素描式的观照,我想说,他的诗是具有现代性的。正如著名诗歌评论家陈超所说:“思乡病,现代诗的一个基本母题。”他进一步说:“有些诗人找到的是精神避难的伊甸园,另一些诗人却寻找另一种更危险的精神家乡。前者以安适为终的,后者以历险为终的。前者自恋,后者自审。”(陈超《游荡者说》之《1987-1995,蓝皮笔记本》)
那么,对照建光的诗歌,我们不难判断,他的“思乡”、他的“乡愁”不是构建避难的“伊甸园”,不是为了安适、自恋,而是自审的,是为了构建一个精神家乡。
关于诗歌的抒情性
诗歌的特质是抒情毋庸置疑。如何把饱满的情感融入诗歌的文本,落实在具体的细节、意象中,这是每一个诗人都不得不面对的问题。建光炙热的情感,有时候达到了炽烈的程度,对于一般诗者来说,可能会大喊大叫了,要火山喷发了。但是建光的诗却采取了“低调”的处理,隐忍而节制,语言虽显疏散随意,文字稍显散漫直陈,情感却做了很好的控制。已经做到了让细节说话,让事件述说,让意象呈现,具有了诗的张力和美感,使诗歌充满了艺术感染力,从而打动、感动读者。
因此,就诗歌的潜质上,建光是具备的;书写的方向上,建光无疑也是正确的。要始终找准一个点儿,坚持不懈地钻进,要有耐心、信心和决心。而我认为,做到这些也不是很难,关键是要具备一种心态。不过,在他的《回声》一诗中,已经让我们看到了他心际的表白,我相信并期待着:
我做我尘世的那一抹残阳
你做你清爽自然的那一座高山
心底一遍遍向你道声再见
你却在一场又一场的雨里
把我的思念化为回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