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日期:2021年09月17日
一条“行走”的鱼儿
——吴晓《黑鱼白鱼》出版背后的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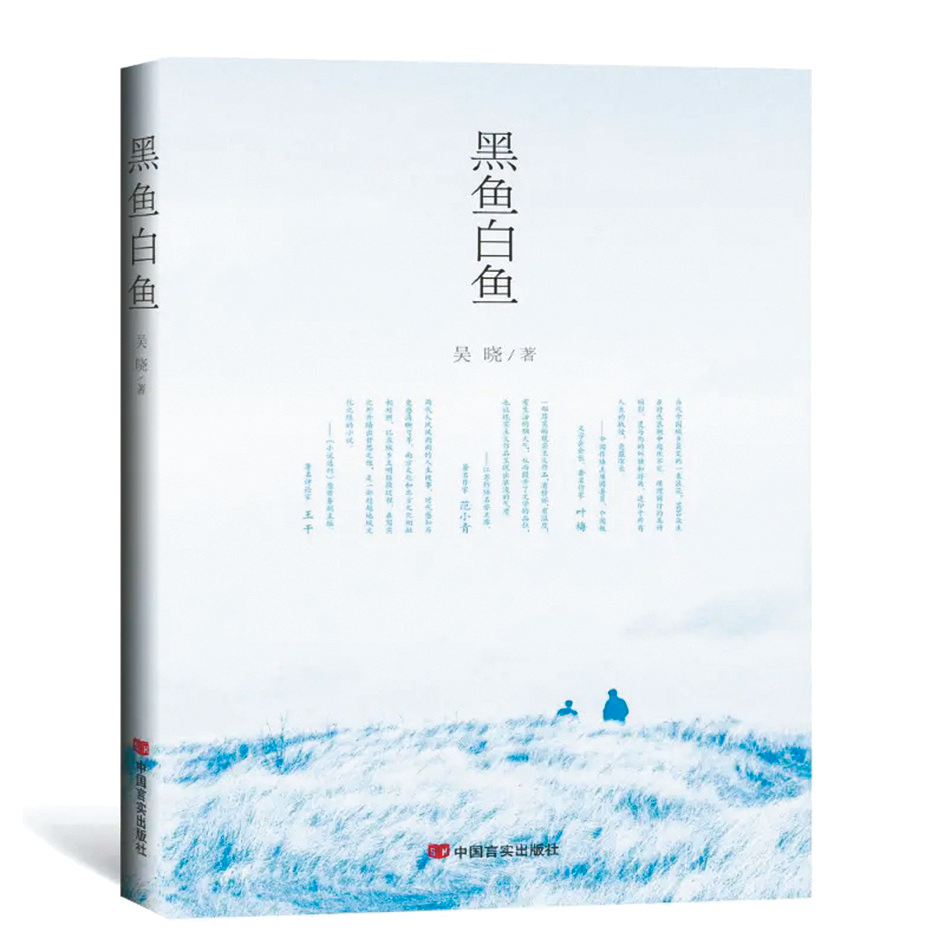
文/图全媒体记者 郭建光
父子两代,互为镜像;黑鱼白鱼,首尾相依。近日,由泌阳籍作家吴晓创作的长篇小说《黑鱼白鱼》由中国言实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引发了较大的社会反响,并得到当代著名作家的点评。
吴晓是驻马店泌阳人,现居江苏江阴。2010年开始文学创作,作品散见于《短篇小说》《小小说选刊》《啄木鸟》《百花园》《莽原》等刊物,并有作品入选初、高中试卷及多个年度选本。小小说《象牙刀》获得《百花园》2013年原创优秀奖。个人荣获“2014年全国小小说十大新秀”称号。
吴晓是一个全职母亲,相夫教子之余,她用手中的笔,抒发着对生活的无比热爱。
走得再远 根在泌阳
在吴晓心中,家乡情结特别浓。这些年她随着丈夫到江苏江阴,相夫教子,一个人撑起了半边天。可是在面临多次抉择时,她还是把户口留在泌阳。
“不迁户口是我的一种情结,为这个我付出了一些代价,比如孩子读幼儿园进不了公立,差的私立幼儿园又不想去,只好每学期花一万多元的学费读好点儿的私立幼儿园。其实我的经济状况并不好,孩子爸爸一个人挣钱,养着我们五口人。不是没想过把户口迁过来,也去管户籍的片警那里咨询过,他把迁户口的流程都详细地给我写在纸条上,并鼓励我:迁过来吧,很简单的,网上就能搞定。就这我还是拖延着没迁。”吴晓表示,大的是一对双胞胎儿子,上学那会儿他们夫妻还没有能力在江阴买房子、落户口,俩儿子是在农民工学校读的小学,偏远乡镇里读的中学,现在他们一个读高三,一个读专科。
她很感谢江阴这座城市,用她的话说就是这座原本陌生的城市收留了他们,并给了他们家一个安稳的生活环境。
今年她再次遇到同样的艰难抉择。她的小女儿明年就要上小学了,如果不把户口迁过来,她就有可能上不了家门口的学校。“已经很急迫了,即使这样我还是抱着侥幸心理,先不迁,赌一把,万一孩子不会被分流到别的区,我又可以把户口安稳地留在泌阳了。”在她的潜意识里觉得一旦把户口迁走,就和故乡那块土地从形式上割裂开了。另一个层面说,把户口留在泌阳,等同于把自己留在了泌阳,留在了老父亲和大弟弟身边。
艰难困苦 玉汝于成
一九七八年农历十一月二十日,大雪纷飞中吴晓出生了。
吴晓21岁那年母亲去世,那时最小的弟弟14岁,小妹15岁,傻弟弟18岁。
据长辈们说傻弟弟小时候又好看又乖巧,特别招人喜欢。六个月时得了脑炎,那是个缺医少药的年代,病毒没有被控制住,不仅毁坏了他的身体,也毁坏了他的大脑,他现在四十多岁了生活还不能完全自理,要父亲给他做饭、洗衣服、洗澡……灵魂却依然是那个被封印在成人身体里的娃娃,继续单纯地爱着每个家人,爱着这个世界。
他大概是世界上最纯净的人,也是吴晓最想保护的人。吴晓在自己的作品里不停地安置他的生活,他是《黑鱼白鱼》里单纯美好的残疾孩子顺顺;他还是吴晓正在创作着的长篇《喜鹊》里的傻安华。这两部作品里都出现了同一座山,叫无力山。这是很矛盾的事,山怎么会无力呢?无力了又怎么会形成山?这恰是吴晓的真实心理写照,意念如此强大,现实中的又如此无力。
吴晓的父亲是民间泥塑艺人,确切说是塑神像的画匠。她的父母是初中同学,感情很好。在吴晓的记忆里,大弟弟六个月之前,他们家是最普通的乡村人家,有着农家人最质朴的情怀与最打动人心的亲情,有木讷勤谨的爷爷,慈善和蔼的奶奶,会讲故事的三爷爷,负责给全家人做饭的爱脸红的长辫子小姑姑,还有一个很爱她的姥姥,和一个一直独身的大舅舅。
吴晓在姥姥家住到三岁,三岁时姥姥去世了,她才回到了自己家。这个时候大弟弟已经生病了,他生病之后全家人都不愉快,又对未来隐隐抱着希望,希望奇迹出现:大弟弟不再软面饼子似的躺着,能站起来走路了。
“这种既不愉快又不失信念的感觉一直伴随着我,让我从很小的时候就对人生有了更多的体察,这可能是我后来从事写作的一个因。”吴晓说。但这个“因”是隐性的,是一颗种子被包在坚硬外壳里,没有合适的土壤,及干湿度,它可能一直都在硬壳里包着。直到吴晓8岁时,看见同龄玩伴去上学,也跟母亲闹着要去上学。父母一合计还是把她送到了学校,先上的育红班。有个老师叫王凤林(也可能是王丰林),六十来岁。
春天时,王老师脖子里挂着一面小黑板,领着孩子们走很远的路去梨树林,把小黑板挂在梨树上,教孩子们认字,认春天的“春”。那个时期的孩子们心性是释放的,愿意去探索感知美好事物,这大概是吴晓最初接受的文学启蒙。
再后来吴晓和几个年龄大、悟性好些的孩子被王老师送去一年级插班。
“我迷迷瞪瞪上完了小学。唯一让我觉得自豪的是我作文写得很好,经常被老师当堂朗读。有一次元旦,我的一篇作文和高年级学哥学姐们的作文一起被裱糊在大街的宣传墙上。逢集,乡亲们站在跟前看,我自豪得不行,算是我发表的第一篇文章吧。”吴晓说,这件事对她的影响很大,也就是那个时候在她心目中扎下文学的种子,至于何时长成参天大树,还需要岁月的打磨与时光的浇灌。
痛失亲人 陷入抑郁
在吴晓16岁那年家里发生了变故,一车村民坐着村长的拖拉机去修路,转弯时吴晓的小姑和堂姑从车上掉了下来,当时小姑躺地上不能动弹,堂姑当时看着没什么事,自己站起来,还说要大家不要管她。过了两天,看起来伤得并不重的堂姑却死了,原来她伤了内脏。
堂姑去世时只有16岁,和吴晓是同年生的。
看完了受伤的小姑回到家里,天已经黑了。这个时期吴晓的爷爷患有食道癌晚期,不能进食,他拉着吴晓瘦小的手跟说他全身都疼,不停地呻吟。吴晓两眼泪花,拖着小小的身子一个人到镇上给爷爷买止疼药。去镇上有两里地的路,要经过坟场。那个晚上的夜很黑。买了药,还买了药酒,回家给爷爷擦背。爷爷瘦骨嶙峋,眼窝深陷,能够感觉到他的身体微微颤抖。
“我牢牢地记着当时的感受,我擦着擦着想逃跑,逃离我所有的亲人,我无法直面他们的苦难,也无力支撑我自己。”第二天吴晓就不想去上学了,爷爷奶奶硬要她去。她在学校里心不在焉,没过几天,爷爷就不行了。
接触文学 人生改变
那个时期,吴晓一方面想努力学习,不辜负家人对她的期望,另一面像丢了魂儿一样,失去了对这个世界的热情和兴趣,课间她时常用衣服蒙着头趴课桌上睡觉,一动不动。
一天清晨,吴晓起床时头疼欲裂,一时间竟然失去了意识。当时到医院开始当脑炎治,后来当癫痫治,都没有治好。后来才知道是因为那个时期她经常一动不动地缩脖子趴着,得了颈椎病,和轻度脑动脉痉挛,血液供不上去,大脑会缺血氧。
就在这个时期吴晓接触到了文学作品,是城里表哥送送给她的,有《收获》《今古传奇》《故事会》《大众电影》等杂志,还有长篇小说《苦菜花》《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她在混沌中看见了另一个世界,一个完全不同于现实生活的世界,她在阅读的过程中一点点儿滋生出和这个世界对抗的力气。
中招考试,她差三分没有考上中专。后来,吴晓的母亲顶着很大的经济压力供她去郑州一所民办学校读预科大专。用吴晓的话,“我把家里的积蓄掏空了。”再后来吴晓认识了一个姓孙的校友,商丘夏邑人,也热爱文学,后来两人走到了一起。
后来,吴晓的母亲得了甲亢,又引发了心脏病。
母亲去世时,吴晓的小妹妹和小弟弟都休学了,一个十五岁,一个十六岁。
“妈妈出殡时的棺材都是四邻凑钱买的。我的人生陷入了两难,留在家里,照顾家人,然后再在附近随便找个婆家嫁了。当真的这么决定时,商丘的孙同学不顾一切来到我家住下不走了。那个时期,我,我奶,我爹,我的弟弟妹妹,还有孙同学,我们在一起过了一小段难得平静的生活。”再后来吴晓得到了小舅的支持,再次离开了家。先是进工厂,再后来从工厂出来四处打零工,当过后勤,保姆,做过钟点工,后来结婚后跟丈夫一起开办了一家很小的保洁公司。随后把小弟弟也带了出来,再后来涉足建筑装潢业,日子渐渐好起来。
几年前她的小弟也开始单干了,他凭着自己的精明能干,很快组建起了自己的团队,每年都有不菲的收入。
2010年生活安稳下来后,吴晓开始写作,随笔,短篇小说,写了就发在榕树下网站。其中有一个短篇是写给奶奶的,叫《我那遥远的沙河调》,被《麦子时光》杂志选载。后来,她就把另一个短篇投给了《短篇小说》杂志,名字叫《盲点》。再以后又给《短篇小说》投了一个短篇,叫《十里铺.豌豆坡》,再次被录用,并发在了头条位置。
当投第三、四篇时,稿子全都石沉大海了。吴晓开始反思自己,写作不能光凭才情和激情,一定要经受专业训练。她开始从小小说写起,一边在网上参加郑州的小小说网络培训,一边大量地阅读,受益匪浅。写了几年小小说后有了想写长篇的念头,写了几万字又搁置了起来。就在这个时候生了小女儿,继续一边带孩子一边阅读、写作,写短篇。
就这样,那部长篇就被她彻底搁置了起来,直到今年《黑鱼白鱼》正式出版。
《黑鱼白鱼》是一部现实主义题材长篇小说,以父子两代人价值观的冲撞为楔子,以他们的爱情故事及截然相反的出走经历为镜像,以"忏悔"和"寻找"两个主题为脉线,时间跨越了半个世纪,场景从乡村切换到城市,再从城市切换到乡村,用中国画的点染手法,塑造了常泾、常云亭、薛巧云、葛青黎、叶北漍等生动人物形象,故事情节上跌宕曲折,可读性强。同时,作者在写作中恰当地使用了豫南和苏南方言,使得书中的人物形象、故事场景更加丰富完整,颇具魅力,既增强了作品的地域文化气息,又还原了豫南的乡村生活和苏南的城镇韵味,极具感染力。
中国作协主席团委员、中国散文学会会长、著名作家 叶梅表示,长篇小说《黑鱼白鱼》是吴晓的扛鼎之作,她的经验与思考在显而易见的娴熟描写里得以呈现。小说的故事人物由世间无数悲欢喧嚣之中精心挑剔而出,纷杂细腻而又鲜活沉重,是当代中国城乡巨变的一束浪花,也是芸芸众生在时代浪潮中起伏不定、蹀躞前行的某种缩影,意蕴深长。
江苏作协名誉主席、著名作家范小青称《黑鱼白鱼》是一部厚实的现实主义作品,有情怀,有温度,有生活的烟火气,从而提升了文学的品位,也让现实主义作品呈现出浪漫的气质。
《小说选刊》原常务副主编、著名评论家王干称,吴晓的小说以浓烈的现实主义腔调讲述了两代人风风雨雨的人生故事,时代感和历史感清晰可寻,南方文化和北方文化相融相对照,记录城乡文明转换过程,在写实之外升腾出哲思之维,是一部超越地域文化之限的小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