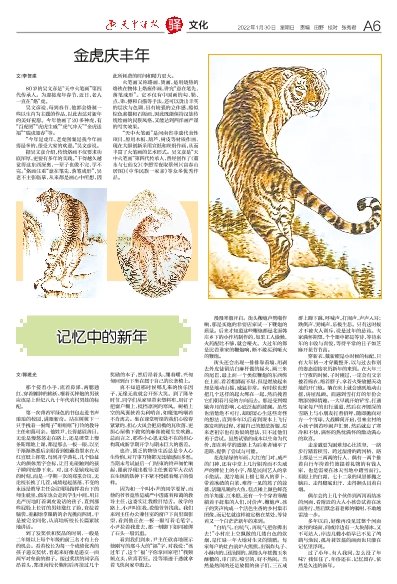发布日期:2022年01月30日
记忆中的新年
文/郭建光
那个搓着小手、流着鼻涕、两腮通红、穿着臃肿的棉袄、嚷着买摔炮的男孩应该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农村男娃的标配。
第一次背着军绿色的书包走进书声琅琅的校园,满眼新奇。站在树桩下一只手拽着一根绳子“哐哐哐”打铃的教导主任和蔼可亲。他姓尹,长得慈眉善目,无论是慢悠悠走在路上,还是课堂上慢条斯理地上课,都是那么一板一眼,以至于渐渐熟悉后亲眼看到他蘸着墨水在大红宣纸上挥毫,每到开学典礼,几个脸盆大的颜体黑字会标,让目光碰触到的孩子瞬间安静下来。对,这不是嬉戏玩耍的时刻,而是一学期一次的郑重会议,无论校长换了几茬,成绩起起落落,不变的永远是教导主任会议现场指挥着台下的师生就坐,偶尔也会走到学生中间,用目光严厉地盯着调皮说话的孩子,直到那些屁股上长钉的男娃涨红了脸,耷拉着脑袋,羞赧地拿眼睛的余光挑向四周,于是被完全同化,认真地听校长长篇累牍地讲话。
到了发奖状和奖品的时刻,一般是二年级以上每个年级的前三名才有上台的机会。看着校长为每一个成绩优秀的孩子递交奖状,看起来好像是递交一面两军对垒前的旗子。接过奖状的同学高昂着头,郑重向校长鞠躬后再接过几个奖励的本子,然后昂着头、绷着嘴,兴匆匆回到台下坐在属于自己的长条椅上。
真不知道那时候哪儿来的快乐因子,无缘无故就会开怀大笑。到了隆冬时节,同学们从家里带来塑料布,用钉子把窗户糊上,抵挡凛冽的寒风。树梢上空的风裹挟着尖利哨音,如魔鬼呜咽着不肯离去。坐在课堂听课的我们心收得紧紧的,担心大风会把房檐的瓦吹落,更担心屋檐下做窝的麻雀被硬生生吹跑。总而言之,那些小心思无处不在的担心构筑成新学期开学与期末巨大的落差。
也许,匮乏的物资生活总是令人心生怜悯,对万事万物都无比敏感而多愁。当期末考试最后一门结束的铃声匆忙响起,眼前浮现出教导主任裹着军大衣站在生锈的铁钟下不紧不慢摇着绳子的模样。
因为和一个叫小尹的同学要好,而他的爷爷竟然是威严中透露着和蔼的教导主任,这委实让我瞠目结舌。放学的路上,小尹叫住我,说他爷爷找我。我们来到主任办公兼住室的窗户下向里面张望,看到他正在一板一眼写着毛笔字。小尹拉着我进去,那一刻脚下如同被绑了石头一般沉重。
看到我们到来,尹主任欣喜地展示他刚写的那斗大的“福”字,对我说:“该过年了,这个‘福’字你拿回家吧!”我频频点头,欣喜若狂。没等墨迹干透就拿着飞快向家中跑去。
漫漫寒假开启。街头鞭炮声劈啪作响,那是买炮的非要店家试一下鞭炮的质量。后来才知道这些鞭炮都是北面韩庄乡下的小作坊制作的,如果工人偷懒,火药配比不够,就会哑火。大过年的都是比着谁家的鞭炮响,断不敢买到哑火的鞭炮。
街头还会出现一排排靠着墙,用剥去外皮徒留洁白麻杆做的起火,两三米的尾巴,最上面一个类似鞭炮的东西绑在上面,看着粗鄙而不堪,但是燃放起来却是地动山摇,威猛非常。有时候也想把几个这样的起火绑在一起,然后拽着它们朝着月亮的方向而去。那是受到嫦娥奔月的影响,心底泛起的波澜。虽然也清楚绝不可行,却屡屡心生这些奇怪的想法,直到多年以后看到课本上飞行器发明的过程,才被自己的想法折服,原来老祖宗也有类似的想法,只不过他们勇于尝试。虽然试错的成本以生命为代价,却在科学的道路上为后来者铺平了道路,提供了尝试与可能。
花花绿绿的年画,大红的门对,威严的门神,还有中堂上几行娟秀而不失威严的牌位上的小字,都是民间艺人的拿手绝活。泥泞地面上横七竖八的萝卜、带着冰碴的白菜、难得一见的蔫了的蒜薹、活蹦乱跳的大鱼,糕点摊上颜色鲜亮的羊角蜜、江米糕,还有一个个穿着寒酸揣着手赶集的人们,讨价声、鞭炮声、孩子的笑声构成一个活色生香的乡村集市图像,而记忆就这样被定格在某处,等待着又一个白茫茫新年的来到。
“白吭气,白吭气,再吭气把你撵出去!”小村庄上空飘散的几缕白色的炊烟,是忙碌一年大地对生灵的馈赠。每家每户的灶台前炉火熊熊,出锅炸丸子、小酥肉的,团汤圆的,蒸馒头年糕做玉米酥糖的,串门的,喷空的,好不热闹。当然最热闹的还是放假的孩子们,三五成群上蹿下跳,呼喊声,打闹声,声声入耳;跌倒声、哭喊声,乐极生悲。只有这时候才不被大人训斥,说是过年的忌讳。大家满怀期望,个个眼中都是等待,等待来年的丰收与喜悦,等待平常的日子如芝麻开花节节高。
穿新衣、戴新帽是小时候的标配,只有大年初一才穿戴整齐,以与过去作别的姿态迎接农历新年的来到。在大年三十守夜的时候,子时刚过,一定会有父亲披着棉衣,缩着脖子,拿着火柴放撼天动地的开门炮。躺在床上就会感到地动山摇,房屋乱颤。而遇到雪打灯的年份会增添别样情趣,一大早就开始铲雪,打通每家每户的出行通道,然后在齐腰深的雪路上与小朋友打着招呼,随即抛向对方一个雪球,大战瞬间开启,引来全村的小孩子朝着吵闹声汇聚,然后就忘了寒冷和不快,满怀的热忱满怀的激动满心的欢喜。
走亲戚更为困难却心比铁坚,一路步行踏着积雪,跨过湿滑的跨河桥,路上都是三三两两的行人,偶有一两个推着自行车挎着竹篮提着礼物的有钱人家,也是需要在冰天雪地中踏雪而行。眉眼上的白霜,七十二泉的风景都抛之脑后,走得脚底出汗,走得额头冒着白烟。
偶尔会约上几个伙伴到西河看结冰的河面,看附近的大人小孩尝试着在冰面滑行,然后默念着老师的嘱咐,不敢越雷池一步。
多年以后,好像再没见过整个河面冰封的场面,间或岸边有一大块薄冰,又不可站人,岸边几艘小船早已不见了鸬鹚与渔民,孤舟蓑笠翁的画面也只能在记忆里浮现。
过了小年,有人我问,怎么没了年味?我怔住了,年俗还在,记忆留存,依然是久违的新年。
那个搓着小手、流着鼻涕、两腮通红、穿着臃肿的棉袄、嚷着买摔炮的男孩应该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农村男娃的标配。
第一次背着军绿色的书包走进书声琅琅的校园,满眼新奇。站在树桩下一只手拽着一根绳子“哐哐哐”打铃的教导主任和蔼可亲。他姓尹,长得慈眉善目,无论是慢悠悠走在路上,还是课堂上慢条斯理地上课,都是那么一板一眼,以至于渐渐熟悉后亲眼看到他蘸着墨水在大红宣纸上挥毫,每到开学典礼,几个脸盆大的颜体黑字会标,让目光碰触到的孩子瞬间安静下来。对,这不是嬉戏玩耍的时刻,而是一学期一次的郑重会议,无论校长换了几茬,成绩起起落落,不变的永远是教导主任会议现场指挥着台下的师生就坐,偶尔也会走到学生中间,用目光严厉地盯着调皮说话的孩子,直到那些屁股上长钉的男娃涨红了脸,耷拉着脑袋,羞赧地拿眼睛的余光挑向四周,于是被完全同化,认真地听校长长篇累牍地讲话。
到了发奖状和奖品的时刻,一般是二年级以上每个年级的前三名才有上台的机会。看着校长为每一个成绩优秀的孩子递交奖状,看起来好像是递交一面两军对垒前的旗子。接过奖状的同学高昂着头,郑重向校长鞠躬后再接过几个奖励的本子,然后昂着头、绷着嘴,兴匆匆回到台下坐在属于自己的长条椅上。
真不知道那时候哪儿来的快乐因子,无缘无故就会开怀大笑。到了隆冬时节,同学们从家里带来塑料布,用钉子把窗户糊上,抵挡凛冽的寒风。树梢上空的风裹挟着尖利哨音,如魔鬼呜咽着不肯离去。坐在课堂听课的我们心收得紧紧的,担心大风会把房檐的瓦吹落,更担心屋檐下做窝的麻雀被硬生生吹跑。总而言之,那些小心思无处不在的担心构筑成新学期开学与期末巨大的落差。
也许,匮乏的物资生活总是令人心生怜悯,对万事万物都无比敏感而多愁。当期末考试最后一门结束的铃声匆忙响起,眼前浮现出教导主任裹着军大衣站在生锈的铁钟下不紧不慢摇着绳子的模样。
因为和一个叫小尹的同学要好,而他的爷爷竟然是威严中透露着和蔼的教导主任,这委实让我瞠目结舌。放学的路上,小尹叫住我,说他爷爷找我。我们来到主任办公兼住室的窗户下向里面张望,看到他正在一板一眼写着毛笔字。小尹拉着我进去,那一刻脚下如同被绑了石头一般沉重。
看到我们到来,尹主任欣喜地展示他刚写的那斗大的“福”字,对我说:“该过年了,这个‘福’字你拿回家吧!”我频频点头,欣喜若狂。没等墨迹干透就拿着飞快向家中跑去。
漫漫寒假开启。街头鞭炮声劈啪作响,那是买炮的非要店家试一下鞭炮的质量。后来才知道这些鞭炮都是北面韩庄乡下的小作坊制作的,如果工人偷懒,火药配比不够,就会哑火。大过年的都是比着谁家的鞭炮响,断不敢买到哑火的鞭炮。
街头还会出现一排排靠着墙,用剥去外皮徒留洁白麻杆做的起火,两三米的尾巴,最上面一个类似鞭炮的东西绑在上面,看着粗鄙而不堪,但是燃放起来却是地动山摇,威猛非常。有时候也想把几个这样的起火绑在一起,然后拽着它们朝着月亮的方向而去。那是受到嫦娥奔月的影响,心底泛起的波澜。虽然也清楚绝不可行,却屡屡心生这些奇怪的想法,直到多年以后看到课本上飞行器发明的过程,才被自己的想法折服,原来老祖宗也有类似的想法,只不过他们勇于尝试。虽然试错的成本以生命为代价,却在科学的道路上为后来者铺平了道路,提供了尝试与可能。
花花绿绿的年画,大红的门对,威严的门神,还有中堂上几行娟秀而不失威严的牌位上的小字,都是民间艺人的拿手绝活。泥泞地面上横七竖八的萝卜、带着冰碴的白菜、难得一见的蔫了的蒜薹、活蹦乱跳的大鱼,糕点摊上颜色鲜亮的羊角蜜、江米糕,还有一个个穿着寒酸揣着手赶集的人们,讨价声、鞭炮声、孩子的笑声构成一个活色生香的乡村集市图像,而记忆就这样被定格在某处,等待着又一个白茫茫新年的来到。
“白吭气,白吭气,再吭气把你撵出去!”小村庄上空飘散的几缕白色的炊烟,是忙碌一年大地对生灵的馈赠。每家每户的灶台前炉火熊熊,出锅炸丸子、小酥肉的,团汤圆的,蒸馒头年糕做玉米酥糖的,串门的,喷空的,好不热闹。当然最热闹的还是放假的孩子们,三五成群上蹿下跳,呼喊声,打闹声,声声入耳;跌倒声、哭喊声,乐极生悲。只有这时候才不被大人训斥,说是过年的忌讳。大家满怀期望,个个眼中都是等待,等待来年的丰收与喜悦,等待平常的日子如芝麻开花节节高。
穿新衣、戴新帽是小时候的标配,只有大年初一才穿戴整齐,以与过去作别的姿态迎接农历新年的来到。在大年三十守夜的时候,子时刚过,一定会有父亲披着棉衣,缩着脖子,拿着火柴放撼天动地的开门炮。躺在床上就会感到地动山摇,房屋乱颤。而遇到雪打灯的年份会增添别样情趣,一大早就开始铲雪,打通每家每户的出行通道,然后在齐腰深的雪路上与小朋友打着招呼,随即抛向对方一个雪球,大战瞬间开启,引来全村的小孩子朝着吵闹声汇聚,然后就忘了寒冷和不快,满怀的热忱满怀的激动满心的欢喜。
走亲戚更为困难却心比铁坚,一路步行踏着积雪,跨过湿滑的跨河桥,路上都是三三两两的行人,偶有一两个推着自行车挎着竹篮提着礼物的有钱人家,也是需要在冰天雪地中踏雪而行。眉眼上的白霜,七十二泉的风景都抛之脑后,走得脚底出汗,走得额头冒着白烟。
偶尔会约上几个伙伴到西河看结冰的河面,看附近的大人小孩尝试着在冰面滑行,然后默念着老师的嘱咐,不敢越雷池一步。
多年以后,好像再没见过整个河面冰封的场面,间或岸边有一大块薄冰,又不可站人,岸边几艘小船早已不见了鸬鹚与渔民,孤舟蓑笠翁的画面也只能在记忆里浮现。
过了小年,有人我问,怎么没了年味?我怔住了,年俗还在,记忆留存,依然是久违的新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