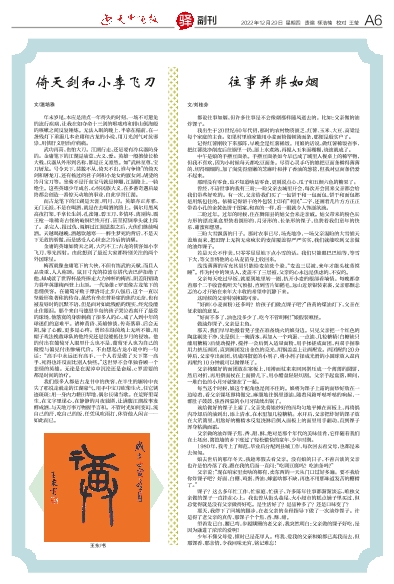发布日期:2022年12月29日
往事并非如烟
文/刘桂芬
都说往事如烟,但许多往事是不会像烟那样随风逝去的。比如:父亲做的油炸馃子。
我出生于20世纪60年代初,那时的农村物资匮乏,红薯、玉米、大豆、高粱是每个家庭的主食。如果村里谁家能用小麦面粉做顿汤面条,那便是殷实户了。
记得红薯刚收下来那阵,早晚全是红薯稀饭。用娘的话说,做红薯稀饭省事,把红薯洗净削皮后往锅里一扔,添上水煮熟,再搅入玉米面糊糊,烧滚就成了。
中午是娘的手擀豆面条。手擀豆面条如今早已成了城里人餐桌上的稀罕物,但我不喜欢,因为小时候每天都吃豆面条。尽管心灵手巧的娘把豆面条檊得薄薄的、切得细细的,加了淘洗得滑嫩的芝麻叶和拌了香油的葱花,但我对豆面条仍爱不起来。
那时没有零食,也不知道啥是零食,更别说点心、瓜子和五颜六色的糖果了。
曾经,不谙世事的我有三盼:一盼父亲去城里开会,每次开会回来父亲都会给我们带些好吃的。有一次,父亲给我们买了一包饼干和一包面包,饼干和面包都是用纸包住的。依稀记得饼干的外包装上印有“利民”二字,还画着几片方方正正带着小孔的金黄色饼干图案,和真的一样,看一眼就令人馋涎欲滴。
二盼过年。过年的时候,住在舞阳县的姑父会来走亲戚。姑父带来的粉色长方形的漂亮果盒里装着圆形的、月牙形的、长条形的馃子,也装着我们童年的快乐、甜蜜和想望。
三盼大雪飘落的日子。那时农事已尽,场光地净,一场父亲渴盼的大雪铺天盖地而来,把田野上无拘无束疯长的麦苗覆盖得严严实实,我们就能吃到父亲做的油炸馃子。
若是天公不作美,只零零星星地下点小雪的话。我们只能眼巴巴地等,等雪下大,等父亲将他的心从麦苗身上收回来。
浅浅薄薄的雪充其量只能给麦苗洗个脸,“麦盖三层被,来年才能头枕蒸馍睡”。作为村中的领头人,麦盖不了三层被,父亲的心永远是焦虑的、不安的。
父亲每天吃过早饭,就要到地里转一圈,扒开小麦的根部看墒情。每晚都拿着那个二手收音机听天气预报,直到雪片如鹅毛,远山近景银装素裹,父亲那颗忐忑的心才开始在来年大丰收的希望中沉静下来。
这时候的父亲特别和蔼可亲。
“好面﹙小麦面粉﹚还多吗?给孩子们做点馃子吧?”昏黄的煤油灯下,父亲在征求娘的意见。
“好面不多了,油也没多少了,吃今不管明啊!”娘假装嗔怪。
做油炸馃子,父亲是主角。
那天,我们早早地搬着凳子坐在准备烧火的娘身边。只见父亲把一个红色的陶盆刷洗干净,先是倒上一碗清水,再加入一个鸡蛋、一点油、几粒糖精﹙白糖缺只能用糖精﹚后使劲搅拌,搅拌一会后倒入适量面粉,用手揉搓成面团,再双手握拳用力挤压面团,直到面团发出金色的亮光,用锅盖盖上让面醒发。面团醒约20分钟后,父亲拿出面团,切成四指宽的小剂子,将小剂子揉成光滑的小圆球放入盆内再醒约10分钟就可以做馃坯了。
父亲将醒好的面团放在案板上,用擀面杖来来回回擀压成一个薄薄的圆饼,然后对折,再用擀面杖在上面擀几下,用小醋盘轻轻切割。父亲手起盘落,瞬间,一堆白色的小月牙就聚在了一起。
每当这个时候,娘这个配角也是闲不住的。娘将为馃子上霜的面炒好放在一边晾着,看父亲馃坯即将做完,麻溜地往锅里添油,随着风箱呼哒呼哒的响起,一群肚子鼓鼓、焦香四溢的小月牙陆续出锅了。
该给做好的馃子上霜了,父亲先将娘炒好的面均匀地平摊在面板上,再将锅内冷却后的油到出,添上清水,在水里加几粒糖精。水开后,父亲把炸好的馃子放在大笊篱里,用熬好的糖精水反复浇淋后倒入面板上的面里用手翻动,直到馃子浑身粘满面霜。
父亲做的油炸馃子焦、香、甜、酥,绝对是那个年代的美味佳肴,它伴随着我们在土坯房、篱笆墙的乡下度过了轻松愉快的童年、少年时期。
1980年,我考上了师范,毕业后分配到县城工作,每次回去看父母,也都是来去匆匆。
娘去世后的那年冬天,我趁寒假去看父亲。没有娘的日子,不善言谈的父亲也许是怕冷落了我,跟在我的后面一直问:“吃调豆腐吗?吃油条吗?”
父亲说:“现在咱家里卖啥的都有,卖东西的一天从门口过好多遍。要不我给你炸馃子吧?好面、白糖、鸡蛋、香油、蜂蜜啥都不缺,再也不用那味道发苦的糖精了。”
馃子?这么多年忙工作、忙家庭、忙孩子,许多陈年往事都渐渐淡忘,唯独父亲做的馃子一直挂在心上。我也曾从街头巷尾、大小超市的糕点铺子里买过,但总觉得就是没有父亲做得好吃。是生活好了?是品种多了?还是口味变了?
那天,我停下了回城的脚步,在老父亲的全程指导下做了一次油炸馃子。许是得了老父亲的真传,那馃子个个焦、香、酥、甜。
望着发已白、腰已弯,步履蹒跚的老父亲,我突然明白:父亲做的馃子好吃,是因为融进了浓浓的爱啊!
少年不懂父母爱,懂时已是花甲人。疼我、爱我的父亲和娘都已离我而去,但那馃香、那亲情,令我回味无穷,铭记难忘!
都说往事如烟,但许多往事是不会像烟那样随风逝去的。比如:父亲做的油炸馃子。
我出生于20世纪60年代初,那时的农村物资匮乏,红薯、玉米、大豆、高粱是每个家庭的主食。如果村里谁家能用小麦面粉做顿汤面条,那便是殷实户了。
记得红薯刚收下来那阵,早晚全是红薯稀饭。用娘的话说,做红薯稀饭省事,把红薯洗净削皮后往锅里一扔,添上水煮熟,再搅入玉米面糊糊,烧滚就成了。
中午是娘的手擀豆面条。手擀豆面条如今早已成了城里人餐桌上的稀罕物,但我不喜欢,因为小时候每天都吃豆面条。尽管心灵手巧的娘把豆面条檊得薄薄的、切得细细的,加了淘洗得滑嫩的芝麻叶和拌了香油的葱花,但我对豆面条仍爱不起来。
那时没有零食,也不知道啥是零食,更别说点心、瓜子和五颜六色的糖果了。
曾经,不谙世事的我有三盼:一盼父亲去城里开会,每次开会回来父亲都会给我们带些好吃的。有一次,父亲给我们买了一包饼干和一包面包,饼干和面包都是用纸包住的。依稀记得饼干的外包装上印有“利民”二字,还画着几片方方正正带着小孔的金黄色饼干图案,和真的一样,看一眼就令人馋涎欲滴。
二盼过年。过年的时候,住在舞阳县的姑父会来走亲戚。姑父带来的粉色长方形的漂亮果盒里装着圆形的、月牙形的、长条形的馃子,也装着我们童年的快乐、甜蜜和想望。
三盼大雪飘落的日子。那时农事已尽,场光地净,一场父亲渴盼的大雪铺天盖地而来,把田野上无拘无束疯长的麦苗覆盖得严严实实,我们就能吃到父亲做的油炸馃子。
若是天公不作美,只零零星星地下点小雪的话。我们只能眼巴巴地等,等雪下大,等父亲将他的心从麦苗身上收回来。
浅浅薄薄的雪充其量只能给麦苗洗个脸,“麦盖三层被,来年才能头枕蒸馍睡”。作为村中的领头人,麦盖不了三层被,父亲的心永远是焦虑的、不安的。
父亲每天吃过早饭,就要到地里转一圈,扒开小麦的根部看墒情。每晚都拿着那个二手收音机听天气预报,直到雪片如鹅毛,远山近景银装素裹,父亲那颗忐忑的心才开始在来年大丰收的希望中沉静下来。
这时候的父亲特别和蔼可亲。
“好面﹙小麦面粉﹚还多吗?给孩子们做点馃子吧?”昏黄的煤油灯下,父亲在征求娘的意见。
“好面不多了,油也没多少了,吃今不管明啊!”娘假装嗔怪。
做油炸馃子,父亲是主角。
那天,我们早早地搬着凳子坐在准备烧火的娘身边。只见父亲把一个红色的陶盆刷洗干净,先是倒上一碗清水,再加入一个鸡蛋、一点油、几粒糖精﹙白糖缺只能用糖精﹚后使劲搅拌,搅拌一会后倒入适量面粉,用手揉搓成面团,再双手握拳用力挤压面团,直到面团发出金色的亮光,用锅盖盖上让面醒发。面团醒约20分钟后,父亲拿出面团,切成四指宽的小剂子,将小剂子揉成光滑的小圆球放入盆内再醒约10分钟就可以做馃坯了。
父亲将醒好的面团放在案板上,用擀面杖来来回回擀压成一个薄薄的圆饼,然后对折,再用擀面杖在上面擀几下,用小醋盘轻轻切割。父亲手起盘落,瞬间,一堆白色的小月牙就聚在了一起。
每当这个时候,娘这个配角也是闲不住的。娘将为馃子上霜的面炒好放在一边晾着,看父亲馃坯即将做完,麻溜地往锅里添油,随着风箱呼哒呼哒的响起,一群肚子鼓鼓、焦香四溢的小月牙陆续出锅了。
该给做好的馃子上霜了,父亲先将娘炒好的面均匀地平摊在面板上,再将锅内冷却后的油到出,添上清水,在水里加几粒糖精。水开后,父亲把炸好的馃子放在大笊篱里,用熬好的糖精水反复浇淋后倒入面板上的面里用手翻动,直到馃子浑身粘满面霜。
父亲做的油炸馃子焦、香、甜、酥,绝对是那个年代的美味佳肴,它伴随着我们在土坯房、篱笆墙的乡下度过了轻松愉快的童年、少年时期。
1980年,我考上了师范,毕业后分配到县城工作,每次回去看父母,也都是来去匆匆。
娘去世后的那年冬天,我趁寒假去看父亲。没有娘的日子,不善言谈的父亲也许是怕冷落了我,跟在我的后面一直问:“吃调豆腐吗?吃油条吗?”
父亲说:“现在咱家里卖啥的都有,卖东西的一天从门口过好多遍。要不我给你炸馃子吧?好面、白糖、鸡蛋、香油、蜂蜜啥都不缺,再也不用那味道发苦的糖精了。”
馃子?这么多年忙工作、忙家庭、忙孩子,许多陈年往事都渐渐淡忘,唯独父亲做的馃子一直挂在心上。我也曾从街头巷尾、大小超市的糕点铺子里买过,但总觉得就是没有父亲做得好吃。是生活好了?是品种多了?还是口味变了?
那天,我停下了回城的脚步,在老父亲的全程指导下做了一次油炸馃子。许是得了老父亲的真传,那馃子个个焦、香、酥、甜。
望着发已白、腰已弯,步履蹒跚的老父亲,我突然明白:父亲做的馃子好吃,是因为融进了浓浓的爱啊!
少年不懂父母爱,懂时已是花甲人。疼我、爱我的父亲和娘都已离我而去,但那馃香、那亲情,令我回味无穷,铭记难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