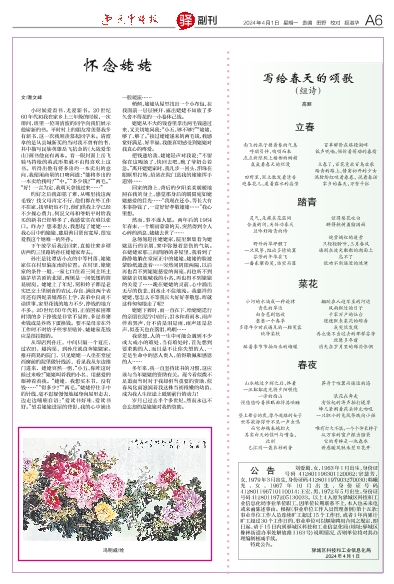发布日期:2024年04月01日
怀念姥姥
文/谭文峰
小时候爱看书,尤爱新书。20世纪60年代初我在家乡上三年级的时候,一次课间,班里一位叫清波的同学向我们展示他崭新的书。平时村上的朋友常羡慕我多有新书,这一次我则羡慕起同学来。清波拿的是从县城新买的当时我不曾有的书,其中描写民族英雄岳飞抗金的《大战爱华山》画书他竟有两本。看一眼封面上岳飞骑马持枪的英武形象就不由得喜欢上这书。听得出他有将多出的一本卖出的意向,我便用商量的口吻问道:“能将多出的一本卖给我吗?”“中。”“多少钱?”“两毛。”“好!一言为定,我明天拿钱过来……”
约好之后我却犯了难,从哪里找这两毛钱?找父母肯定不行,他们都在外工作不在家,找爷奶也不行,他们供我上学已经不少操心费力,何况父母和爷奶平时给我买的新书已经够多了,我感觉实在难以张口。咋办?想来想去,我想起了姥姥……我心目中的姥姥,慈眉善目贤良宽厚,很宠爱我这个她唯一的外孙。
下午放学后我没回家,直接往家乡谭店西约三里路的孙庄姥姥家奔去。
孙庄是比谭店小点的中等村落,姥姥家住在村里偏东南的位置。在村里,姥姥家的条件一般,一家七口住着三间土坯土墙茅草苫顶的北屋,西侧是一间低矮的简易厨房。姥姥上了年纪,舅和妗子都是老实巴交土里刨食的农民,存良、满良两个表哥还有四妮表姐都在上学,表弟中良尚不谙世事,家里花钱的地方不少,挣钱的地方不多。20世纪60年代初,正值国家困难时期的乡下挣钱是非常不易的,多是养猪卖钱或是养鸡下蛋换钱。要不是母亲在外工作时不时给予些零星贴补,姥姥家花钱应是很拮据的。
从谭店到孙庄,中间只隔一个夏庄,过农田、越沟渠,到孙庄就直奔姥姥家。推开简易的院门,只见姥姥一人坐在堂屋西窗前的院里做针线活,看见我从东边推门进来,姥姥突然一愣,“小五,你咋这时候过来啦?”姥姥叫着我的小名,用慈爱的眼神看着我。“姥姥,我想买本书,没有钱……”“得多少?”“两毛。”姥姥停住手中的针线,毫不迟疑慢慢地起身向屋里走去,边走边喃喃自语:“爱读书好哇,爱读书好。”望着姥姥进屋的背影,我的心中涌出一股暖流……
稍倾,姥姥从屋里找出一个小布包,在我面前一层层展开,露出姥姥不知放了多久舍不得花的一小卷体己钱。
姥姥从不大的钱卷里拿出两毛钱递过来,又关切地问我:“小五,够不够?”“姥姥,够了,够了。”接过姥姥递来的两毛钱,我感觉好满足、好幸福,我能真切感受到姥姥对我真心的疼爱。
把钱递给我,姥姥轻声对我说:“不留你在这喝汤了,快回去吧,晚了爷奶会着急。”离开姥姥家时,我几步一回头,泪珠在眼眶里打转,给站在院门送我的姥姥挥手道别……
回家的路上,背后的夕阳柔柔暖暖地照在我的身上,感觉那身后的暖阳宛如姥姥慈爱的目光……“我现在还小,等长大有本事挣钱了,一定好好孝敬姥姥……”我心里想。
然而,事不遂人愿。两年后的1964年春末,一个细雨蒙蒙的天,突然得到令人心碎的消息,姥姥去世了……
急匆匆赶往姥姥家,院里聚集着为姥姥送行的亲朋,家中弥漫着悲伤的气氛。在姥姥家那三间简陋的茅屋里,我看到了静静地躺在堂屋正中的姥姥,姥姥的脸被蒙脸纸遮盖着……突然间阴阳两隔,以后再也看不到姥姥慈爱的面庞,再也听不到姥姥亲切地喊我的小名,再也得不到姥姥的关爱了……跪在姥姥的灵前,心中涌出无尽的伤悲,泪水止不住地流。我慈祥的姥姥,您怎么不等我长大好好孝敬您,咋就这样匆匆地走了呢?
姥姥下葬时,雨一直在下,给姥姥送行的亲朋在泥泞中前行,泪水和着雨水,雨声伴着哭声,分不清是泪是雨,雨声还是悲声,似苍天也在落泪、呜咽……
我常想,人的一生中可能会遇到不少或大或小的难处,当有难处时,首先想到要求助的人,而且是不让你失望的人,一定是生命中的恩人贵人,值得敬佩和感恩的人……
多年来,我一直坚持读书的习惯,这应该与当年姥姥的资助有关。现今看似微不足道而当时对于我却相当重要的资助,似春风化雨滋润着我这株当初稚嫩的幼苗,成为我人生征途上砥砺前行的动力!
岁月已过去半个多世纪,然而永远不会忘却的是姥姥对我的资助。
小时候爱看书,尤爱新书。20世纪60年代初我在家乡上三年级的时候,一次课间,班里一位叫清波的同学向我们展示他崭新的书。平时村上的朋友常羡慕我多有新书,这一次我则羡慕起同学来。清波拿的是从县城新买的当时我不曾有的书,其中描写民族英雄岳飞抗金的《大战爱华山》画书他竟有两本。看一眼封面上岳飞骑马持枪的英武形象就不由得喜欢上这书。听得出他有将多出的一本卖出的意向,我便用商量的口吻问道:“能将多出的一本卖给我吗?”“中。”“多少钱?”“两毛。”“好!一言为定,我明天拿钱过来……”
约好之后我却犯了难,从哪里找这两毛钱?找父母肯定不行,他们都在外工作不在家,找爷奶也不行,他们供我上学已经不少操心费力,何况父母和爷奶平时给我买的新书已经够多了,我感觉实在难以张口。咋办?想来想去,我想起了姥姥……我心目中的姥姥,慈眉善目贤良宽厚,很宠爱我这个她唯一的外孙。
下午放学后我没回家,直接往家乡谭店西约三里路的孙庄姥姥家奔去。
孙庄是比谭店小点的中等村落,姥姥家住在村里偏东南的位置。在村里,姥姥家的条件一般,一家七口住着三间土坯土墙茅草苫顶的北屋,西侧是一间低矮的简易厨房。姥姥上了年纪,舅和妗子都是老实巴交土里刨食的农民,存良、满良两个表哥还有四妮表姐都在上学,表弟中良尚不谙世事,家里花钱的地方不少,挣钱的地方不多。20世纪60年代初,正值国家困难时期的乡下挣钱是非常不易的,多是养猪卖钱或是养鸡下蛋换钱。要不是母亲在外工作时不时给予些零星贴补,姥姥家花钱应是很拮据的。
从谭店到孙庄,中间只隔一个夏庄,过农田、越沟渠,到孙庄就直奔姥姥家。推开简易的院门,只见姥姥一人坐在堂屋西窗前的院里做针线活,看见我从东边推门进来,姥姥突然一愣,“小五,你咋这时候过来啦?”姥姥叫着我的小名,用慈爱的眼神看着我。“姥姥,我想买本书,没有钱……”“得多少?”“两毛。”姥姥停住手中的针线,毫不迟疑慢慢地起身向屋里走去,边走边喃喃自语:“爱读书好哇,爱读书好。”望着姥姥进屋的背影,我的心中涌出一股暖流……
稍倾,姥姥从屋里找出一个小布包,在我面前一层层展开,露出姥姥不知放了多久舍不得花的一小卷体己钱。
姥姥从不大的钱卷里拿出两毛钱递过来,又关切地问我:“小五,够不够?”“姥姥,够了,够了。”接过姥姥递来的两毛钱,我感觉好满足、好幸福,我能真切感受到姥姥对我真心的疼爱。
把钱递给我,姥姥轻声对我说:“不留你在这喝汤了,快回去吧,晚了爷奶会着急。”离开姥姥家时,我几步一回头,泪珠在眼眶里打转,给站在院门送我的姥姥挥手道别……
回家的路上,背后的夕阳柔柔暖暖地照在我的身上,感觉那身后的暖阳宛如姥姥慈爱的目光……“我现在还小,等长大有本事挣钱了,一定好好孝敬姥姥……”我心里想。
然而,事不遂人愿。两年后的1964年春末,一个细雨蒙蒙的天,突然得到令人心碎的消息,姥姥去世了……
急匆匆赶往姥姥家,院里聚集着为姥姥送行的亲朋,家中弥漫着悲伤的气氛。在姥姥家那三间简陋的茅屋里,我看到了静静地躺在堂屋正中的姥姥,姥姥的脸被蒙脸纸遮盖着……突然间阴阳两隔,以后再也看不到姥姥慈爱的面庞,再也听不到姥姥亲切地喊我的小名,再也得不到姥姥的关爱了……跪在姥姥的灵前,心中涌出无尽的伤悲,泪水止不住地流。我慈祥的姥姥,您怎么不等我长大好好孝敬您,咋就这样匆匆地走了呢?
姥姥下葬时,雨一直在下,给姥姥送行的亲朋在泥泞中前行,泪水和着雨水,雨声伴着哭声,分不清是泪是雨,雨声还是悲声,似苍天也在落泪、呜咽……
我常想,人的一生中可能会遇到不少或大或小的难处,当有难处时,首先想到要求助的人,而且是不让你失望的人,一定是生命中的恩人贵人,值得敬佩和感恩的人……
多年来,我一直坚持读书的习惯,这应该与当年姥姥的资助有关。现今看似微不足道而当时对于我却相当重要的资助,似春风化雨滋润着我这株当初稚嫩的幼苗,成为我人生征途上砥砺前行的动力!
岁月已过去半个多世纪,然而永远不会忘却的是姥姥对我的资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