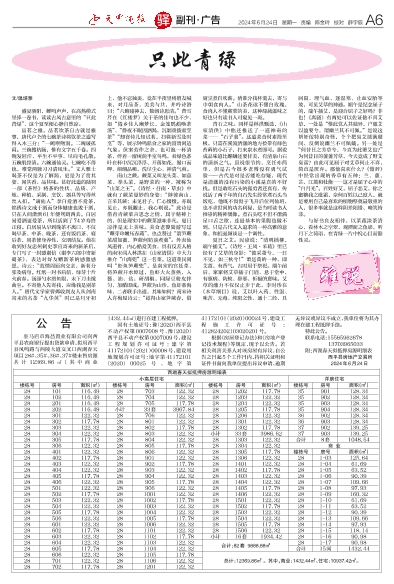发布日期:2024年06月24日
只此青绿
文/温培雅
盛夏骄阳,蝉鸣声声,在高热模式里捧一卷书,读读古风古意里的“只此青绿”,这个夏至便心静自然凉。
品茗之雅。品茗饮茶自古就是雅事,唐代卢仝的七碗茶诗将饮茶之道写得入木三分:“一碗喉吻润。二碗破孤闷。三碗搜枯肠,惟有文字五千卷。四碗发轻汗,平生不平事,尽向毛孔散。五碗肌骨清。六碗通仙灵。七碗吃不得也,唯觉两腋习习清风生。”文人雅士喝茶不仅是为了解渴,更是为了赏其姿、闻其香、品其味。甚好此道的陆羽一部《茶经》将茶的性状、品质、产地、种植、采制、烹饮、器具等写得丝丝入扣。“谪仙人”李白爱酒不爱茶,锦绣诗文成于酒而身体健康也败于酒,只在人间潇洒61年便驾鹤西去。白居易爱酒更爱茶,所以活到了74岁寿终正寝。白居易从早到晚茶不离口,不仅喝早茶、中茶、晚茶,还有饭后茶、寝后茶,用茶修身养性、交朋结友。他在收到好友忠州刺史李宣寄来的新茶后,专门写了一封感谢信《谢李六郎中寄新蜀茶》,表达对好友赠新茶的感激感恩,诗云:“故情周匝向交亲,新茗分张及病身。红纸一封书后信,绿芽十片火前春。汤添勺水煎鱼眼,末下刀圭搅曲尘。不寄他人先寄我,应缘我是别茶人。”唐代文学家曹邺收到友人从剑南寄来的名茶“九华英”时已是月牙初上,他不忍独美,竟在半夜里将僧友喊来,对月品茶,美美与共,并吟诗赞曰:“六腑睡神去,数朝诗思清。”曹雪芹在《红楼梦》关于茶的佳句也不少,如“倦乡佳人幽梦长,金笼鹦鹉唤茶汤”、“静夜不眠因酒渴,沉烟重拨索烹茶”“却喜侍儿知试茗,扫将新雪及时烹”等,展示钟鸣鼎食之家的富贵闲适气象。伏案劳作之余,也可泡一杯清茶,伴着一窗树荫半室鸟鸣,看绿色茶叶在杯中沉沉浮浮、开落如花,撮口而呷、细细品咂,洗尽尘心、神清气爽。
南山之蕨。蕨菜又叫龙头菜、如意菜、拳头菜,是野菜的一种,被称为“山菜之王”。《诗经·召南·草虫》中就有了蕨菜曼妙的身姿:“陟彼南山,言采其蕨;未见君子,仁心惙惙。亦既见止,亦既觏止,我心则说。”此诗是借青青蕨菜言思念之情,属于精神上的,但是现实中的蕨菜滋味非凡,夏日凉拌是无上美味。美食老饕陆游写过“蕨芽珍嫩压春蔬”,也点赞过“箭笋蕨菜甜如蜜,笋蕨何妨谈煮羹”。外表仙风道骨、内心酷爱美食,具有反差人格的南宋词人林洪在《山家清供》中大力推介“山海兜”这一名菜。这道菜民间叫“虾鱼笋蕨兜”,是南宋的宫廷菜,将笋蕨开水焯过,鱼虾大火蒸熟,入酱、油、盐,研胡椒,同绿豆粉皮拌匀,加醋即成。笋蕨为山珍,鱼虾系海味,二者联手出道,其味如何?南宋诗人许梅屋诗云:“趁得山家笋蕨春,借厨烹煮自吹薪。倩谁分我杯羹去,寄与中朝食肉人。”山茶花读不懂白玫瑰,食肉人不懂蕨菜的美,这种绿蔬滋味之好也只有读书人可窥见一斑。
青石之味。同样是林洪甄选,《山家清供》中他还推送了一道神奇的菜——“石子羹”。这道菜食材素简至极,只需在溪流清澈的地方捡带有绿色苔藓的小石子,打来泉水煮即可。据说成品味道比螺蛳还要甘美,有清泉山石的清新之气。虽说很节约,烹饪亦简单,但是古今很多老餮没有勇气试验——古代是对是否能吃存疑,现代是清澈的没有污染的小溪是真的不好找。但是敢吃石头的孤勇者还真有,传说活了两千年的白石先生经常煮石头当饭吃,他既不汲汲于飞升后位列仙班,也不求世间的功名利禄,是当时读书人推崇的精神偶像。煮石头吃不但不能满足口舌之欲,连最基本的果腹也做不到,只是古代文人追求的一种高雅的意象,和扪虱倾谈是一个调性。
夏日之艾。民谚说:“清明插柳,端午插艾”。《诗经·王风·采葛》里已经有了艾草的身影:“彼采萧兮,一日不见,如三秋兮!”萧是蒿的一种,即艾蒿,有香气,古时用于祭祀。端午前后,家家将艾草插于门眉,悬于堂中,有驱病、防蚊、辟邪、祈福的意味。艾草的能力不仅仅止步于此,李时珍在《本草纲目》说,艾以叶入药,性温、味苦、无毒、纯阳之性、通十二经、具回阳、理气血、逐湿寒、止血安胎等效,可见艾草的神通。端午是纪念屈子的,端午插艾,是迎合屈子之好吗?非也!《离骚》有两处可以佐证他不喜艾草,一处是“惟此党人其独异,户服艾以盈要兮,谓幽兰其不可佩。”是说这帮奸佞特别奇怪,个个把臭艾插满腰间,反倒说幽兰不可佩戴。另一处是“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为此萧艾也?”为何昔日的萋萋芳草,今天竟成了野艾臭蒿?由此可见屈子对艾草何止不喜,简直是厌弃。那他喜欢什么?《楚辞》中经常出现的香草有五种:兰、蕙、芷、江蓠和杜衡——这才是屈子心中的“白月光”。百姓好艾,屈子恶艾,你之蜜糖我之砒霜,奈何百姓以己度人,就是要用自己最喜欢的植物祭奠最敬重的人,很多事就是这样阴差阳错、啼笑皆非。
与好书良友相伴,以菜蔬淡茶清心,看林木之空翠,观潭面之鱼影,听月下之荷语,在青绿一片中悦心目而豁性灵。
盛夏骄阳,蝉鸣声声,在高热模式里捧一卷书,读读古风古意里的“只此青绿”,这个夏至便心静自然凉。
品茗之雅。品茗饮茶自古就是雅事,唐代卢仝的七碗茶诗将饮茶之道写得入木三分:“一碗喉吻润。二碗破孤闷。三碗搜枯肠,惟有文字五千卷。四碗发轻汗,平生不平事,尽向毛孔散。五碗肌骨清。六碗通仙灵。七碗吃不得也,唯觉两腋习习清风生。”文人雅士喝茶不仅是为了解渴,更是为了赏其姿、闻其香、品其味。甚好此道的陆羽一部《茶经》将茶的性状、品质、产地、种植、采制、烹饮、器具等写得丝丝入扣。“谪仙人”李白爱酒不爱茶,锦绣诗文成于酒而身体健康也败于酒,只在人间潇洒61年便驾鹤西去。白居易爱酒更爱茶,所以活到了74岁寿终正寝。白居易从早到晚茶不离口,不仅喝早茶、中茶、晚茶,还有饭后茶、寝后茶,用茶修身养性、交朋结友。他在收到好友忠州刺史李宣寄来的新茶后,专门写了一封感谢信《谢李六郎中寄新蜀茶》,表达对好友赠新茶的感激感恩,诗云:“故情周匝向交亲,新茗分张及病身。红纸一封书后信,绿芽十片火前春。汤添勺水煎鱼眼,末下刀圭搅曲尘。不寄他人先寄我,应缘我是别茶人。”唐代文学家曹邺收到友人从剑南寄来的名茶“九华英”时已是月牙初上,他不忍独美,竟在半夜里将僧友喊来,对月品茶,美美与共,并吟诗赞曰:“六腑睡神去,数朝诗思清。”曹雪芹在《红楼梦》关于茶的佳句也不少,如“倦乡佳人幽梦长,金笼鹦鹉唤茶汤”、“静夜不眠因酒渴,沉烟重拨索烹茶”“却喜侍儿知试茗,扫将新雪及时烹”等,展示钟鸣鼎食之家的富贵闲适气象。伏案劳作之余,也可泡一杯清茶,伴着一窗树荫半室鸟鸣,看绿色茶叶在杯中沉沉浮浮、开落如花,撮口而呷、细细品咂,洗尽尘心、神清气爽。
南山之蕨。蕨菜又叫龙头菜、如意菜、拳头菜,是野菜的一种,被称为“山菜之王”。《诗经·召南·草虫》中就有了蕨菜曼妙的身姿:“陟彼南山,言采其蕨;未见君子,仁心惙惙。亦既见止,亦既觏止,我心则说。”此诗是借青青蕨菜言思念之情,属于精神上的,但是现实中的蕨菜滋味非凡,夏日凉拌是无上美味。美食老饕陆游写过“蕨芽珍嫩压春蔬”,也点赞过“箭笋蕨菜甜如蜜,笋蕨何妨谈煮羹”。外表仙风道骨、内心酷爱美食,具有反差人格的南宋词人林洪在《山家清供》中大力推介“山海兜”这一名菜。这道菜民间叫“虾鱼笋蕨兜”,是南宋的宫廷菜,将笋蕨开水焯过,鱼虾大火蒸熟,入酱、油、盐,研胡椒,同绿豆粉皮拌匀,加醋即成。笋蕨为山珍,鱼虾系海味,二者联手出道,其味如何?南宋诗人许梅屋诗云:“趁得山家笋蕨春,借厨烹煮自吹薪。倩谁分我杯羹去,寄与中朝食肉人。”山茶花读不懂白玫瑰,食肉人不懂蕨菜的美,这种绿蔬滋味之好也只有读书人可窥见一斑。
青石之味。同样是林洪甄选,《山家清供》中他还推送了一道神奇的菜——“石子羹”。这道菜食材素简至极,只需在溪流清澈的地方捡带有绿色苔藓的小石子,打来泉水煮即可。据说成品味道比螺蛳还要甘美,有清泉山石的清新之气。虽说很节约,烹饪亦简单,但是古今很多老餮没有勇气试验——古代是对是否能吃存疑,现代是清澈的没有污染的小溪是真的不好找。但是敢吃石头的孤勇者还真有,传说活了两千年的白石先生经常煮石头当饭吃,他既不汲汲于飞升后位列仙班,也不求世间的功名利禄,是当时读书人推崇的精神偶像。煮石头吃不但不能满足口舌之欲,连最基本的果腹也做不到,只是古代文人追求的一种高雅的意象,和扪虱倾谈是一个调性。
夏日之艾。民谚说:“清明插柳,端午插艾”。《诗经·王风·采葛》里已经有了艾草的身影:“彼采萧兮,一日不见,如三秋兮!”萧是蒿的一种,即艾蒿,有香气,古时用于祭祀。端午前后,家家将艾草插于门眉,悬于堂中,有驱病、防蚊、辟邪、祈福的意味。艾草的能力不仅仅止步于此,李时珍在《本草纲目》说,艾以叶入药,性温、味苦、无毒、纯阳之性、通十二经、具回阳、理气血、逐湿寒、止血安胎等效,可见艾草的神通。端午是纪念屈子的,端午插艾,是迎合屈子之好吗?非也!《离骚》有两处可以佐证他不喜艾草,一处是“惟此党人其独异,户服艾以盈要兮,谓幽兰其不可佩。”是说这帮奸佞特别奇怪,个个把臭艾插满腰间,反倒说幽兰不可佩戴。另一处是“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为此萧艾也?”为何昔日的萋萋芳草,今天竟成了野艾臭蒿?由此可见屈子对艾草何止不喜,简直是厌弃。那他喜欢什么?《楚辞》中经常出现的香草有五种:兰、蕙、芷、江蓠和杜衡——这才是屈子心中的“白月光”。百姓好艾,屈子恶艾,你之蜜糖我之砒霜,奈何百姓以己度人,就是要用自己最喜欢的植物祭奠最敬重的人,很多事就是这样阴差阳错、啼笑皆非。
与好书良友相伴,以菜蔬淡茶清心,看林木之空翠,观潭面之鱼影,听月下之荷语,在青绿一片中悦心目而豁性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