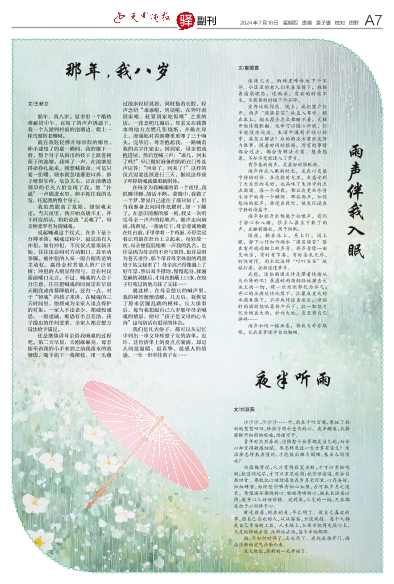发布日期:2024年07月18日
那年,我八岁
文/王新立
那年,我八岁。夏季里一个酷热难耐的中午,在知了的声声诱惑下,我一个人溜到村前的池塘边,爬上一株弯腰的老柳树。
就在我轻轻拂开绿帘似的柳丝,伸手逮知了的那一瞬间,我的脚下一滑,整个身子从斜出的枝干上跌进树荫下的池塘。我叫了一声,在池塘里拼命挣扎起来。我想喊救命,可是只要一张嘴,塘水就忽地灌进口鼻,鼻子呛得生疼。危急关头,正在池塘边割草的毛头大伯发现了我。他“扑通”一声跳进水里,伸手抓住我的头发,托起我的整个身子。
我虽然脱离了危险,却惊魂未定。当天夜里,我开始高烧不止,并不时说胡话。奶奶说我“丢魂了”,母亲便张罗着为我喊魂。
说起喊魂这个仪式,在乡下是十分神圣的。喊魂过程中,最忌讳有人冲犯。如有冲犯,不仅仪式要重新开始,往往还会向对方动粗口,甚至动拳脚。被冲犯的人家一般占据舆论的主动权,赢得全村其他人的广泛同情;冲犯的人则显得理亏,会在村民面前哑口无言。不过,喊魂的人会十分注意,往往把喊魂的时间定在早晨天刚亮或夜幕降临时。还有一点,对于“掉魂”的孩子来讲,在喊魂的三天时间里,他将成为全家人重点保护的对象。一家人不论老少,都诚惶诚恐,一脸虔诚,唯恐有半点差池,孩子提出的任何要求,全家人都会想方设法给予满足。
还是继续讲母亲给我喊魂的过程吧。第二天早晨,天刚麻麻亮,母亲便牵着我的小手来到之前我落水的池塘边,随手掐下一截柳枝,用一头蘸过池水轻轻晃着,同时拖着长腔,轻声念叨“乖乖啦,听话啦,在外吓着回家啦,赶紧回家吃饭喽”之类的话。一连念叨几遍后,母亲又在我落水的地方点燃几张烧纸,并跪在岸上,虔诚地对着池塘重重叩了三个响头。完毕后,母亲抱起我,一路喊着我的名字往家走。回到家,母亲把我抱进屋,然后连喊三声:“乖儿,回来了吗?”早已做好准备的奶奶在门外连声应答:“回来了,回来了!”这样的仪式需要连续进行三天,据说这样孩子吓掉的魂就能重新附体。
在母亲为我喊魂的第一个夜里,我似睡非睡,胡话不断。蒙眬中,我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逮住了那只知了。但当我准备去向同伴炫耀时,却一下醒了。在意识清醒的那一刻,我又一次听见母亲一声声的轻唤声。循声走向厨房,我看见,一盏油灯下,母亲虔诚地跪在灶台前,手里拿着一个鸡蛋,不停尝试着让鸡蛋在灶台上立起来。每轻放一次,母亲便低低地唤一声我的乳名。也许是因为母亲的不舍与坚持,也许是因为苍天垂怜,那个带着母亲体温的鸡蛋终于站立起来了!母亲高兴得像遇上了好年景,然后双手撑地,慢慢起身,揉遍发麻的双膝后,才用食指蘸上口水,在蚊子叮咬过的地方抹了又抹……
就这样,在母亲悠长的喊声里,我的神智渐渐清醒。几天后,我恢复了原来活蹦乱跳的模样。长大懂事后,每当我想起自己八岁那年母亲喊魂的情景,便对“孩子是父母的心头肉”这句俗话有更深的体会。
我们是凡夫俗子,都可以从记忆中列出一串父母疼爱子女的清单。也许,这份清单上的爱点点滴滴,却是人间最温暖、最真挚、最感人的情感,一生一世牵挂着子女……
那年,我八岁。夏季里一个酷热难耐的中午,在知了的声声诱惑下,我一个人溜到村前的池塘边,爬上一株弯腰的老柳树。
就在我轻轻拂开绿帘似的柳丝,伸手逮知了的那一瞬间,我的脚下一滑,整个身子从斜出的枝干上跌进树荫下的池塘。我叫了一声,在池塘里拼命挣扎起来。我想喊救命,可是只要一张嘴,塘水就忽地灌进口鼻,鼻子呛得生疼。危急关头,正在池塘边割草的毛头大伯发现了我。他“扑通”一声跳进水里,伸手抓住我的头发,托起我的整个身子。
我虽然脱离了危险,却惊魂未定。当天夜里,我开始高烧不止,并不时说胡话。奶奶说我“丢魂了”,母亲便张罗着为我喊魂。
说起喊魂这个仪式,在乡下是十分神圣的。喊魂过程中,最忌讳有人冲犯。如有冲犯,不仅仪式要重新开始,往往还会向对方动粗口,甚至动拳脚。被冲犯的人家一般占据舆论的主动权,赢得全村其他人的广泛同情;冲犯的人则显得理亏,会在村民面前哑口无言。不过,喊魂的人会十分注意,往往把喊魂的时间定在早晨天刚亮或夜幕降临时。还有一点,对于“掉魂”的孩子来讲,在喊魂的三天时间里,他将成为全家人重点保护的对象。一家人不论老少,都诚惶诚恐,一脸虔诚,唯恐有半点差池,孩子提出的任何要求,全家人都会想方设法给予满足。
还是继续讲母亲给我喊魂的过程吧。第二天早晨,天刚麻麻亮,母亲便牵着我的小手来到之前我落水的池塘边,随手掐下一截柳枝,用一头蘸过池水轻轻晃着,同时拖着长腔,轻声念叨“乖乖啦,听话啦,在外吓着回家啦,赶紧回家吃饭喽”之类的话。一连念叨几遍后,母亲又在我落水的地方点燃几张烧纸,并跪在岸上,虔诚地对着池塘重重叩了三个响头。完毕后,母亲抱起我,一路喊着我的名字往家走。回到家,母亲把我抱进屋,然后连喊三声:“乖儿,回来了吗?”早已做好准备的奶奶在门外连声应答:“回来了,回来了!”这样的仪式需要连续进行三天,据说这样孩子吓掉的魂就能重新附体。
在母亲为我喊魂的第一个夜里,我似睡非睡,胡话不断。蒙眬中,我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逮住了那只知了。但当我准备去向同伴炫耀时,却一下醒了。在意识清醒的那一刻,我又一次听见母亲一声声的轻唤声。循声走向厨房,我看见,一盏油灯下,母亲虔诚地跪在灶台前,手里拿着一个鸡蛋,不停尝试着让鸡蛋在灶台上立起来。每轻放一次,母亲便低低地唤一声我的乳名。也许是因为母亲的不舍与坚持,也许是因为苍天垂怜,那个带着母亲体温的鸡蛋终于站立起来了!母亲高兴得像遇上了好年景,然后双手撑地,慢慢起身,揉遍发麻的双膝后,才用食指蘸上口水,在蚊子叮咬过的地方抹了又抹……
就这样,在母亲悠长的喊声里,我的神智渐渐清醒。几天后,我恢复了原来活蹦乱跳的模样。长大懂事后,每当我想起自己八岁那年母亲喊魂的情景,便对“孩子是父母的心头肉”这句俗话有更深的体会。
我们是凡夫俗子,都可以从记忆中列出一串父母疼爱子女的清单。也许,这份清单上的爱点点滴滴,却是人间最温暖、最真挚、最感人的情感,一生一世牵挂着子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