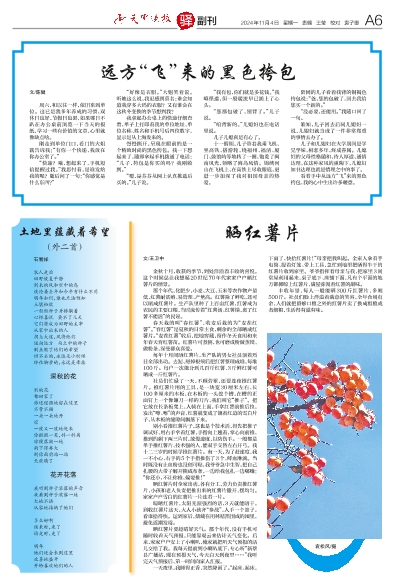发布日期:2024年11月04日
晒红薯片
文/王卫中
金秋十月,收获的季节,到处洋溢着丰收的喜悦。这个时候总让我想起20世纪70年代家家户户晒红薯片的情景。
那个年代,化肥少,小麦、大豆、玉米等农作物产量低,红薯耐贫瘠、易管理、产量高。红薯除了鲜吃,还可以晒成红薯片。生产队里种了上百亩红薯,红薯成为农民的主要口粮,当时流传着“红薯汤、红薯馍,离了红薯不能活”的民谣。
春天栽的叫“春红薯”,收麦后栽的为“麦茬红薯”。“春红薯”是夏秋的日常主食,剩余的全部晒成红薯片。“麦茬红薯”收后,挖地窖藏,留作冬天食用和来年春天育红薯苗。红薯片可煮粥,也可磨成粉做蒸馍、做粉条,深受群众喜爱。
每年十月间晒红薯片,生产队的男女社员顶着烈日全部出动。去泥、掰掉根须后把红薯整理成堆,每堆100斤。每户一次能分到几百斤红薯,3斤鲜红薯可晒成一斤红薯片。
社员们忙碌了一天,不顾劳累,还要连夜推红薯片。推红薯片用的工具,是一块宽30厘米左右、长100多厘米的木板,在木板的一头挖个槽,在槽的正面钉上一个像镰刀一样的刀片,我们叫它“推子”。把它放在长条板凳上,人骑在上面,手拿红薯前推后拉,发出“嚓、嚓”的声音,红薯就变成了镶着红边的雪白片子,从木板的缝隙间飘落下来。
别小看推红薯片子,这也是个技术活,得先把推子调试好,用右手拿着红薯,手指向上翘着,掌心向前推,推到约剩下两三片时,放慢速度,以防伤手。一般都是单手推红薯片,技术强的人,能双手交替左右开弓。我十二三岁的时候学推红薯片。有一天,为了赶速度,我一不小心,右手的5个手指推伤了3个,鲜血淋漓。当时既没有止血粉也没创可贴,我爷爷急中生智,把自己扎腰的大带子解开撕成布条,一边给我包扎一边嘟囔:“你还小,不让你推,偏要推!”
晒红薯片时全家出动,各有分工,劳力负责推红薯片,小孩和老人负责把推出来的红薯片撒开,摆均匀。家家户户雪白的红薯片一片连着一片。
晾晒红薯片,太阳光照强烈的话,3天就能晒干。到收红薯片这天,大人小孩齐“参战”,人手一个篮子,看谁拾得快。运到家后,储藏在用秫秸箔围成的囤里,避免返潮发霉。
晒红薯片要趁晴好天气。那个年代,没有手机可随时收看天气预报,只能靠观云来估计天气变化。后来,家家户户安上了小喇叭,俺家就把听天气预报的活儿交给了我。我每天提前到小喇叭底下,专心听“新蔡县广播站,现在预报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我听完天气预报后,第一时间向家人汇报。
一天夜里,我睡得正香,突然降雨了。“起床、起床,下雨了,快拾红薯片!”母亲把我叫起。全家人拿着手电筒、提着灯笼、带上工具,急忙到地里把晒得半干的红薯片收到家里。爷爷指挥着母亲与我,把家里3间堂屋利用起来,桌子底下、床铺下面,凡有个平面的地方都摊晾上红薯片,满屋弥漫着红薯的甜味。
丰收年景,每人一般能晒300斤红薯片,多则500斤。社员们脸上洋溢着满意的笑容,全年食用有余,人们就把留够口粮之外的红薯片卖了换成粗粮或者细粮,生活得有滋有味。
金秋十月,收获的季节,到处洋溢着丰收的喜悦。这个时候总让我想起20世纪70年代家家户户晒红薯片的情景。
那个年代,化肥少,小麦、大豆、玉米等农作物产量低,红薯耐贫瘠、易管理、产量高。红薯除了鲜吃,还可以晒成红薯片。生产队里种了上百亩红薯,红薯成为农民的主要口粮,当时流传着“红薯汤、红薯馍,离了红薯不能活”的民谣。
春天栽的叫“春红薯”,收麦后栽的为“麦茬红薯”。“春红薯”是夏秋的日常主食,剩余的全部晒成红薯片。“麦茬红薯”收后,挖地窖藏,留作冬天食用和来年春天育红薯苗。红薯片可煮粥,也可磨成粉做蒸馍、做粉条,深受群众喜爱。
每年十月间晒红薯片,生产队的男女社员顶着烈日全部出动。去泥、掰掉根须后把红薯整理成堆,每堆100斤。每户一次能分到几百斤红薯,3斤鲜红薯可晒成一斤红薯片。
社员们忙碌了一天,不顾劳累,还要连夜推红薯片。推红薯片用的工具,是一块宽30厘米左右、长100多厘米的木板,在木板的一头挖个槽,在槽的正面钉上一个像镰刀一样的刀片,我们叫它“推子”。把它放在长条板凳上,人骑在上面,手拿红薯前推后拉,发出“嚓、嚓”的声音,红薯就变成了镶着红边的雪白片子,从木板的缝隙间飘落下来。
别小看推红薯片子,这也是个技术活,得先把推子调试好,用右手拿着红薯,手指向上翘着,掌心向前推,推到约剩下两三片时,放慢速度,以防伤手。一般都是单手推红薯片,技术强的人,能双手交替左右开弓。我十二三岁的时候学推红薯片。有一天,为了赶速度,我一不小心,右手的5个手指推伤了3个,鲜血淋漓。当时既没有止血粉也没创可贴,我爷爷急中生智,把自己扎腰的大带子解开撕成布条,一边给我包扎一边嘟囔:“你还小,不让你推,偏要推!”
晒红薯片时全家出动,各有分工,劳力负责推红薯片,小孩和老人负责把推出来的红薯片撒开,摆均匀。家家户户雪白的红薯片一片连着一片。
晾晒红薯片,太阳光照强烈的话,3天就能晒干。到收红薯片这天,大人小孩齐“参战”,人手一个篮子,看谁拾得快。运到家后,储藏在用秫秸箔围成的囤里,避免返潮发霉。
晒红薯片要趁晴好天气。那个年代,没有手机可随时收看天气预报,只能靠观云来估计天气变化。后来,家家户户安上了小喇叭,俺家就把听天气预报的活儿交给了我。我每天提前到小喇叭底下,专心听“新蔡县广播站,现在预报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我听完天气预报后,第一时间向家人汇报。
一天夜里,我睡得正香,突然降雨了。“起床、起床,下雨了,快拾红薯片!”母亲把我叫起。全家人拿着手电筒、提着灯笼、带上工具,急忙到地里把晒得半干的红薯片收到家里。爷爷指挥着母亲与我,把家里3间堂屋利用起来,桌子底下、床铺下面,凡有个平面的地方都摊晾上红薯片,满屋弥漫着红薯的甜味。
丰收年景,每人一般能晒300斤红薯片,多则500斤。社员们脸上洋溢着满意的笑容,全年食用有余,人们就把留够口粮之外的红薯片卖了换成粗粮或者细粮,生活得有滋有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