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日期:
野人怀土 小草恋山
——读吴相渝诗集《尘世的教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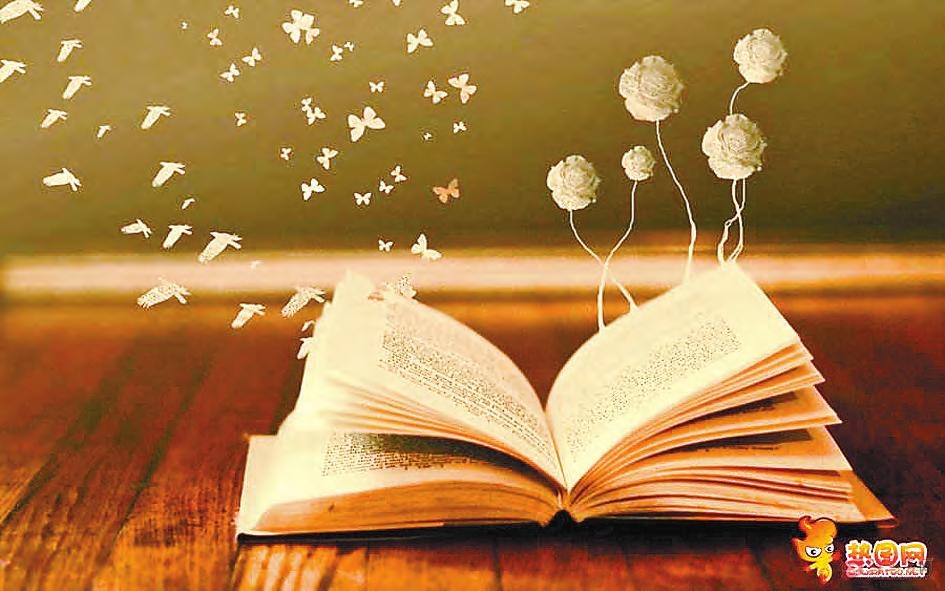
□赵立功
“野人怀土,小草恋山。”是我读吴相渝诗集《尘世的教育》后,想起的鲁迅先生的话。我认为没有比这话更适合来概括作者在这本诗集里所表达的那种——一个农村青年背井离乡,去往城市打拼了一遭后,回归农村故乡的心境了。
作者的这一境遇不是孤例,他是20世纪末和本世纪初中国城市化进程中,成千上万农村青年的生命轨迹和心路历程,这里的城市化,不仅指物质基建层面城市扩张将大量的农村土地兼并吞没,还指城市基于所拥有的文化、物质繁荣而对身处日益凋敝陷落的乡土农村的青年人所激发的向往和逃离,由此带来的对城市身份的转换追求。
但这不是一个顺畅的通道,国家政策的倡导推进与社会结构的艰难调适,之间存在的巨大张力带给无数弃乡进城青年的是,打工求职的生活艰辛和城市屋檐下的精神酸辛。这本诗集的作者,其现实经历和情感经历,即是无数进城者中的一个标本,一个切片。当然,这些现实经历和情感经历是以诗的形式呈现的,从诗歌反映生活的角度说,这本诗集在具象层面完成了它所赋予的诗歌使命。这表现在:
诗歌的内容,对作者的生活和情感做了真实、直接的反映,有时几近自然的暴露,却是对自我内心和对外在世界的一种坦然和诚恳。
从结构上看,四个部分整体上形成了一个打工者从城市回归乡村的叙事言说,这其中,有作为一个进城青年的作者,在城市所感受到的物质和精神的双重挤压的痛苦,有基于这种痛苦而产生的对乡土的思念,有最终回归了乡土,并在乡土踏实而温情的怀抱中回味咀嚼个人过去的痛苦和现在经历的幸福,从而实现了对现代城市所施于一个进城打工者从生活到精神挤压的控诉,完成了一场对尚处贫穷的传统乡土温情脉脉的回望和以城市为代表的现代文明的逆城市化否定。而这也构成了进城打工后又返归乡土的诗人的个我精神和心灵的成长史,诗集名《尘世的教育》内涵也即着力于表达这种成长。
诗歌语言上的朴素、舒展和圆熟。在这本诗集中,作者的诗歌语言是朴素舒展的,朴素呈现给人们的是真实,舒展带给人们的是语感的自然,而圆熟的修辞已经使他能够在保持浓郁的抒情诗风中,在意象的虚实间自由出入和腾挪。当下互联网的发展为语言流通和思维融合提供的便利,理论上使文学的地域身份正面临日益消弭的可能,但身处传统深厚的中原文化场域,作者没有故弄玄虚地追求曾几何时十分流行的诗歌语言和意象的新奇险涩,这反映出其写作的诚实和诗路的纯正。
问题是,仅以可以获得高分的诗艺能完成诗歌之于反映转型中的社会生活的全部使命吗?诗歌的方向有两个,一个是展示自我,吸引社会的目光向我这里看,从而以个我中心的形式起到教人们认识生活的作用;一个是以一己观察和表述,引导人们的目光向社会看,从而起到教人们顺着作者的目光认识生活的作用,前者多的是表达的感性,后者更需要作者的理性。究竟哪种是更为有效的呢?这问题好比感性的唐诗和理性的宋诗哪一个更好,答案只能凭个人和阅读人群的喜好了。
但无论哪一种方向和路子,诗歌本质上都是诗人的一种燃烧,无非前者在燃烧自我,后者在燃烧社会。而自我,往往是有穷的,社会,往往是无穷的。这决定了诗歌的近于远、有穷与无穷,或有限与无限。
相渝和我认识十五六年了,从刚刚到郑州的一个对文学有追求的打工青年,到现在已经有所成就的返乡诗人,中间长期疏于联系,但他一直是个努力的人,在他找我为他的这本诗集写点评论的时候,寂寂如我不敢简慢,愿以上述对他的这本诗集的观感,仅在诗的领域,与他共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