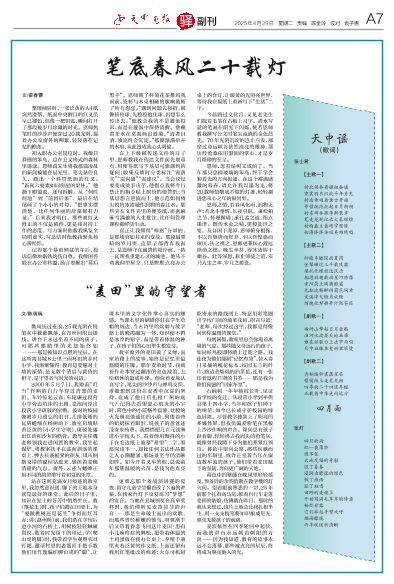发布日期:2025年04月29日
“麦田”里的守望者
文/陈瑞瑞
微风抚过麦浪,25载光阴在粉笔灰中簌簌飘落,在青丝间织出银线。讲台下永远坐着不同的孩子,可那些眼睛里的光却始终如一——那是被知识点燃的星辰。在这所离县城8公里三面环田的乡村小学,我渐渐懂得:教育是麦穗对土地的深情,是无数个清晨与黄昏的相守,是守望者与时光的对话。
2000年5月7日,我蹬着“叮当”作响的自行车穿过青葱的麦田。车铃惊起云雀,车轮碾过段营小学旁边坑洼的土路,麦浪间浮出段营小学斑驳的屋檐。彼时的校园像被岁月遗忘的旧书,几排低矮的瓦房蜷缩在杨树荫下,教室后墙贴着泛黄的《小学生守则》,斑驳处露出红砖和沙灰的筋骨。教导主任魏老师领我走进闲置的教室,我生起煤炉,将教案抚平在漆面剥落的课桌上,掸去长条板凳的积灰,风从钢筋交错的窗棂钻进来,裹挟着麦穗清甜的气息。窗外,云雀与蟋蟀正用不同的韵律谱写着初夏的乐章。
站在这间充满岁月痕迹的教室里,我忽然意识到,脚下的土地本身就是最好的课堂。此后的日子里,知识在泥土的芬芳中悄然生长。教《落花生》时,孩子们蹲在田埂上,为“要做桃树还是花生”争得面红耳赤;讲《赵州桥》前,我们趴在学校后边小河的石桥上,用树枝轻轻触碰裂纹,数着时光留下的印记;学《爬山虎的脚》时,我带着学生观察农具钉耙,邀请村里的老篾匠手把手教他们用竹篾编织爬山虎的“脚”,让课本里的文字化作掌心真实的触感。当课本里的蝴蝶停驻在学生草帽的绒边,当古诗里的炊烟与放学路上的晚霞融为一体,知识便不再是冰冷的铅字,而是带着体温的种子,在孩子们的心田里生根发芽。
教室窗外的麦田黄了又绿,而家访路上的故事,始终是记忆里最温暖的注脚。那年麦收时节,我载着作业本穿过翻滚的金色波浪,去给病休的道成补课。他倚着麦垛认真写字,笔尖的沙沙声与蝉鸣交织,谁能想到这份在麦香中沉淀的坚持,竟成了他日后扎根广州的底气?记得去看望患心肌炎的小宇时,暮色中的小院格外寂静,灶膛的火光照亮他通红的小脸,佝偻着背的奶奶抹着眼泪,说孩子的爸爸还没寄来药费。我悄悄把几百元钱塞进小宇枕头下,看着他用颤抖的小手在毛边纸上临摹“希望”二字,墨痕深浅不一,却比任何书法作品都让人心潮翻涌,那场景至今仍清晰如昨。如今开着叉车的他,总说童年那簇温暖的火苗,是我为他点亮的。
更难忘那个备战演讲赛的夏夜,留守儿童莹莹攥着改了3遍的讲稿,在我家台灯下反复练习“梦想”的发音。当她在县城领奖台高举奖杯时,我仿佛听见麦苗拔节的声音——那是生命破土而出的欢歌,而那些曾经稚嫩的雏鸟,羽翼渐丰后又带着眷恋飞回这片麦田:患有小儿麻痹症的鹤松,把带着体温的土鸡蛋放在我办公桌上,养殖手册里夹着泛黄的作文纸,上面还留有我用红笔批改的痕迹;火车司机赵乾寄来的路线图上,特意用彩笔圈出学校门前的油菜花田,附言写道:“老师,每次经过这里,我都觉得像回到你温暖的课堂。”
每到暑假,教室里总会弥漫着离别的气息。那些随父母远行的孩子,如同候鸟般即将踏上迁徙之路。我连夜为他们缝制“记忆布袋”,装入春日采摘的槐花标本、校园玉兰的叶片、路边金灿灿的油菜花,还有一张印着返程日期的书签——那是我为他们预留的“回家车票”。
石楠树一年年抽枝长叶,见证着学校的变迁。从段营小学到平舆县第十四小学,当年和孩子们种下的树苗,如今已长成守护校园的绿色屏障。尽管教学楼装上了明亮的多媒体屏,但我仍偏爱粉笔在黑板上沙沙作响的声音。课间总有孩子踮着脚,轻轻拂去我肩头的粉笔灰,就像曾经我蹲下身为他们系紧红领巾。暮色中望向公路,那些疾驰而过的车辆里,或许正坐着当年在窗边数车流的孩子,他们带着麦田赋予的坚韧,奔向更广阔的天地。
暮色中的紫藤在晚风里轻轻摇曳,预备铃的余韵消散在教学楼的灯火间。望着眼前熟悉的一切,25年前那个扎着高马尾、推着自行车走进麦田的姑娘,仿佛就在昨日。那时的我从未想过,这片土地会让我扎根半生,用一支支粉笔将知识酿成星光,照亮无数孩子的前路。
麦浪依然在四季轮回中起伏,而我的讲台永远朝着朝阳的方向——因为我知道,教育的故事永远不会落幕,那些被点亮的星辰,终将成为照亮他人的光。
微风抚过麦浪,25载光阴在粉笔灰中簌簌飘落,在青丝间织出银线。讲台下永远坐着不同的孩子,可那些眼睛里的光却始终如一——那是被知识点燃的星辰。在这所离县城8公里三面环田的乡村小学,我渐渐懂得:教育是麦穗对土地的深情,是无数个清晨与黄昏的相守,是守望者与时光的对话。
2000年5月7日,我蹬着“叮当”作响的自行车穿过青葱的麦田。车铃惊起云雀,车轮碾过段营小学旁边坑洼的土路,麦浪间浮出段营小学斑驳的屋檐。彼时的校园像被岁月遗忘的旧书,几排低矮的瓦房蜷缩在杨树荫下,教室后墙贴着泛黄的《小学生守则》,斑驳处露出红砖和沙灰的筋骨。教导主任魏老师领我走进闲置的教室,我生起煤炉,将教案抚平在漆面剥落的课桌上,掸去长条板凳的积灰,风从钢筋交错的窗棂钻进来,裹挟着麦穗清甜的气息。窗外,云雀与蟋蟀正用不同的韵律谱写着初夏的乐章。
站在这间充满岁月痕迹的教室里,我忽然意识到,脚下的土地本身就是最好的课堂。此后的日子里,知识在泥土的芬芳中悄然生长。教《落花生》时,孩子们蹲在田埂上,为“要做桃树还是花生”争得面红耳赤;讲《赵州桥》前,我们趴在学校后边小河的石桥上,用树枝轻轻触碰裂纹,数着时光留下的印记;学《爬山虎的脚》时,我带着学生观察农具钉耙,邀请村里的老篾匠手把手教他们用竹篾编织爬山虎的“脚”,让课本里的文字化作掌心真实的触感。当课本里的蝴蝶停驻在学生草帽的绒边,当古诗里的炊烟与放学路上的晚霞融为一体,知识便不再是冰冷的铅字,而是带着体温的种子,在孩子们的心田里生根发芽。
教室窗外的麦田黄了又绿,而家访路上的故事,始终是记忆里最温暖的注脚。那年麦收时节,我载着作业本穿过翻滚的金色波浪,去给病休的道成补课。他倚着麦垛认真写字,笔尖的沙沙声与蝉鸣交织,谁能想到这份在麦香中沉淀的坚持,竟成了他日后扎根广州的底气?记得去看望患心肌炎的小宇时,暮色中的小院格外寂静,灶膛的火光照亮他通红的小脸,佝偻着背的奶奶抹着眼泪,说孩子的爸爸还没寄来药费。我悄悄把几百元钱塞进小宇枕头下,看着他用颤抖的小手在毛边纸上临摹“希望”二字,墨痕深浅不一,却比任何书法作品都让人心潮翻涌,那场景至今仍清晰如昨。如今开着叉车的他,总说童年那簇温暖的火苗,是我为他点亮的。
更难忘那个备战演讲赛的夏夜,留守儿童莹莹攥着改了3遍的讲稿,在我家台灯下反复练习“梦想”的发音。当她在县城领奖台高举奖杯时,我仿佛听见麦苗拔节的声音——那是生命破土而出的欢歌,而那些曾经稚嫩的雏鸟,羽翼渐丰后又带着眷恋飞回这片麦田:患有小儿麻痹症的鹤松,把带着体温的土鸡蛋放在我办公桌上,养殖手册里夹着泛黄的作文纸,上面还留有我用红笔批改的痕迹;火车司机赵乾寄来的路线图上,特意用彩笔圈出学校门前的油菜花田,附言写道:“老师,每次经过这里,我都觉得像回到你温暖的课堂。”
每到暑假,教室里总会弥漫着离别的气息。那些随父母远行的孩子,如同候鸟般即将踏上迁徙之路。我连夜为他们缝制“记忆布袋”,装入春日采摘的槐花标本、校园玉兰的叶片、路边金灿灿的油菜花,还有一张印着返程日期的书签——那是我为他们预留的“回家车票”。
石楠树一年年抽枝长叶,见证着学校的变迁。从段营小学到平舆县第十四小学,当年和孩子们种下的树苗,如今已长成守护校园的绿色屏障。尽管教学楼装上了明亮的多媒体屏,但我仍偏爱粉笔在黑板上沙沙作响的声音。课间总有孩子踮着脚,轻轻拂去我肩头的粉笔灰,就像曾经我蹲下身为他们系紧红领巾。暮色中望向公路,那些疾驰而过的车辆里,或许正坐着当年在窗边数车流的孩子,他们带着麦田赋予的坚韧,奔向更广阔的天地。
暮色中的紫藤在晚风里轻轻摇曳,预备铃的余韵消散在教学楼的灯火间。望着眼前熟悉的一切,25年前那个扎着高马尾、推着自行车走进麦田的姑娘,仿佛就在昨日。那时的我从未想过,这片土地会让我扎根半生,用一支支粉笔将知识酿成星光,照亮无数孩子的前路。
麦浪依然在四季轮回中起伏,而我的讲台永远朝着朝阳的方向——因为我知道,教育的故事永远不会落幕,那些被点亮的星辰,终将成为照亮他人的光。